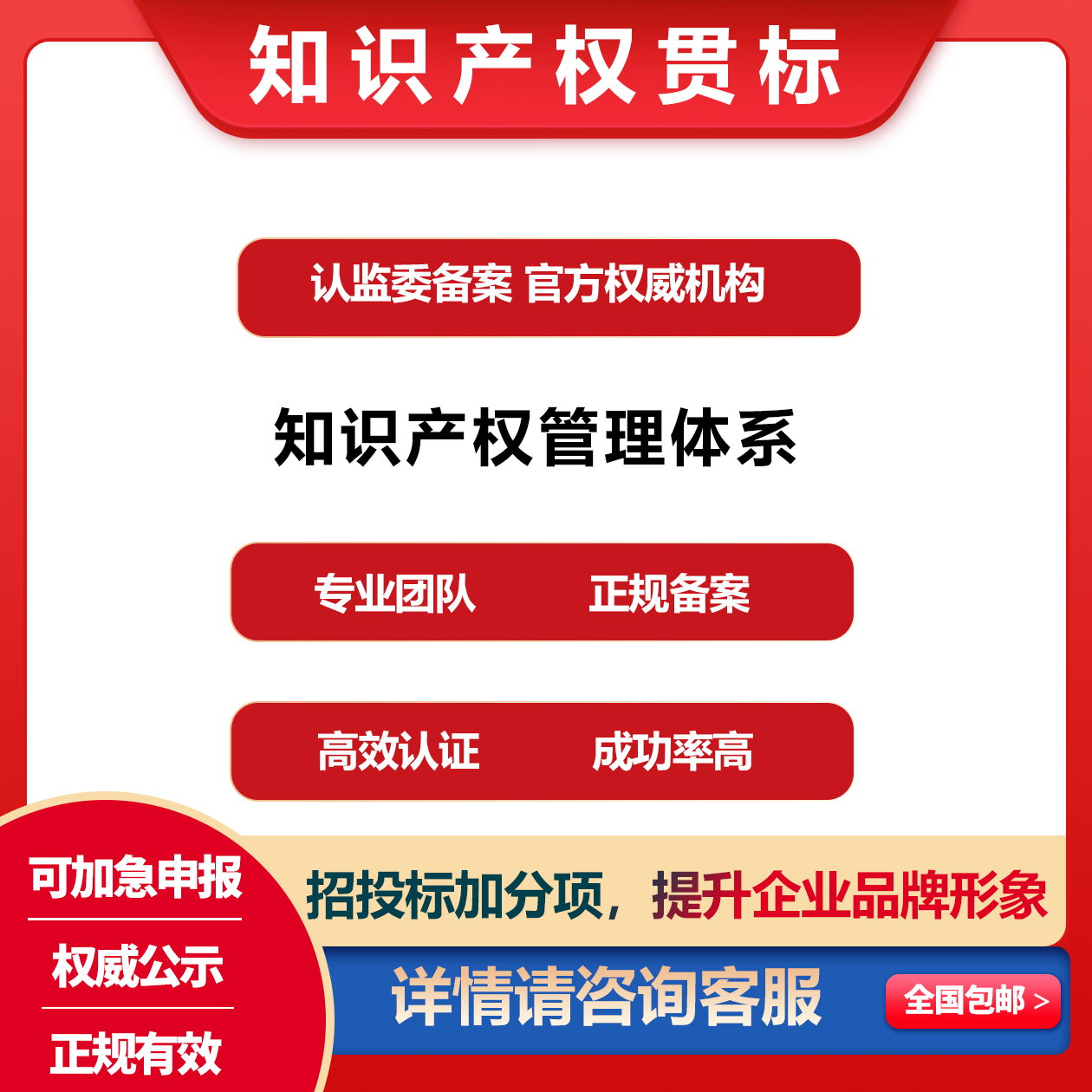知识产权对信息保护的有效性问题
受美国学者约翰?巴洛(JohnPerryBarlow)的版权消亡论的影响,不少学者认为在数字化环境下传统版权法正而临越来越多的困境,已经完全失去存在的价值。有的学者甚至指出,版权法正逐步偏离其鼓励创造,促进知识和文化传播的立法宗旨。SivaVaidhyanathan在《版权丛林》一文中指出,版权越来越强势一一版权客体的扩大、保护程度的增加不仅抑制了个人创作,也妨碍了知识和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而卡罗尔?辛普森也在《版权给你的未来造成困境了吗?)中明确指出,在电子网络时代,版权法已经变得完全不重要了,即便没有强大的版权法保护,知识财产的生产将继续增长。另一方面,DRM、P2P、BL.OG技术的快速发展也给版权法提出了更多的挑战,版权保护和信息公共获取的分歧变得史无前例的尖锐。因此,更多的学者努力探询重建版权制度的法律框架以解决这些题。我们尝试把这些努力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唯技术论派的观点。他们认为:“技术性保护措施的发展进步,将会给予版权作品更好的保护,从而胜于存在于网络空间之外的法律;而合理使用则应当作为1个平衡物来维持公众与私人之间的适度平衡。”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YeeFenLim教授则指出数字权利管理(DigitalRightsManagement,简称DRM)事实上赋予版权人超出法律规定的更多的权力、因此,与版权法相比,DRM给予了版权人更为切实有效的所有权保护香港的李亚虹博士也支持这种观点,她认为实施DRM能够有效保护权利人的权利,因而能够取消版权制度,代之以税收制度。第二,平衡论派的观点。他们认为版权改革在于重建版权系统的平衡。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教授詹姆士?博伊尔(JamesBoyle)认为,“为新闻工作者、教师定义合理使用制度是数字环境下重建版权系统平衡的重要措施。”即便作为创作共同董事会成员,博伊尔也在《开放心态为何重要?》一文中指出,“这不是说开放总是对的,而是我们必须在开放与封闭、专有与免费之间取得平衡。”斯坦福大学的保罗?戈尔斯坦也指出版权利益平衡是考虑数字时代版权领域新问题的立足点。第三,创作共同论派的观点。杰西卡?利特曼(JessicaI.Itman)希望,版权法应当“短期、简单和公平”,在这样的版权法体系下,我们不再根据复制权来定义版权,而是将版权重塑为商业利用的排他权。0劳伦斯?菜斯格(LawrenCELessig)则建议版权法重建应该遵循这几个主要原则:①缩短版权保护期限:②简单的二元体系,取消复杂的例外情况;③强制调整;④禁止延长追溯期限。第四,公共政策论派的观点。哈佛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法教授威廉?·费希尔(WilliamV.Fisher)建议用政府行政补偿来代替版权法的主要部分和加密保护技术。采用税收制度,根据作品的普及范围,从税收中给予进行版权登记的音乐或电影作品权利人对应占比的黯偿。,随着版权保护日益体现出垄断的新趋势,版权保护的垄断化发展已经超出了版权法能够调整的范围,应当采用反断政策进行调整。其次是版权的利益平衡问题。在网络环境下,传统的利益平衡发生了转变,扩大版权人权利、认可技术性保护措施等立法上的转变均显示利益开始逐渐向私人利益倾斜。劳伦斯?菜斯格指出公共领域正在不断缩小。对此,有学者从效益主义哲学(theUtilitarianPhilosophy)的角度研究版权利益平衡问题,指出效益主义要求立法者在计算财产权利时应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在以排他性权利激励发明与艺术作品创作的同时,对该权利限制公众享用那些创造物的偏向子以控制,并力求在者之间实现一种最佳平衡。并且认为效益主义是版权法的价值基础,版权法应该在效益主义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指引下,构建一系列的制度以实现版权人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平衡。克里斯蒂娜?汉纳也在《版权回归》一文中强调版权法发展的趋势是版权人权利的扩大,而公众获取信息的空间却在缩小。版权法中公共利益与权利人利益的紧张对立主要体现在版权侵权案例中,这是由于版权法对于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规定很模糊。而所谓版权回归,就是要缩小私人利益的范围,扩充公共利益的范围,仅有这样才能达到新的平衡。国内学者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知识产权的“对价”与“衡平”理论,认为知识产权机制的运行就是“对价”ー一平等个体之间自由与自由让渡和补偿的平衡,以此实现冲突双方处于帕累托最优状况时的帕累托改进,即不损害任何别人的自由而对别人的自由进行改善。DRM的发展与应用使得版权人和公众利益的冲突再次尖锐·面临新的挑战多数学者认为DRM给版权利益平衡原则带来新的冲击,从实质上减小了合理使用的有效性。信息技术政策办公室(OfficeforInformationTechnologyPolicy,OITP)的戈德温(Godwin)认为DRM会约束公众对于受DRM保护的信息的合法使用,例如公共领城作品的获取(或其他容许自由使用的作品)图书馆作品的保存、行生作品的创作、历史的研究、合理使用权利的行使以及为教学目的的使用。除此之外,过度的技术保护还容易使那些在网络技术开发和网络资源运营方面具有强大优势的企业缺乏约束,从而可能出现滥用技术措施,损害消费者和竟争厂商的利益。大卫?曼恩(DavidMann)在题为《数字权利管理和失明者》一文中,表达了他对于DRM技术负面效应的担忧。他指出,盲人或其他残疾人原本能够借助辅助阅读技术实现信息获取,今日他们也会由于DRM而被拒之门外。大英图书馆馆长林恩?布林德利(1.ynneBrindley)发起了一次有关数字时代版权利益平衡的辩论,他认为DRM技术发展、版权强化使得公众合理使用的权利受到侵犯,提醒立法者注意版权法的修改要协调好技术措施、版权保护与公共获取、共享知识和信息三者间的平衡。最后是版权扩张的合理性问题。为了应对以因特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环境给版权保护带来的问题,各国纷纷修改版权法以适应数字环境。这一轮版权法案的调整凸昆了版权强化和扩张的趋势,也引起了学术界对于版权扩张合理性的探讨。多数学者认为,现代版权扩张法案打破了传统版权法的衡平性而没有使社会公众获得补偿。威廉?霍兰德(WilliamHollander)认为,“RIAA向国会施加压力修改版权法,使得版权得以持续扩张,给予版权人更多的保护,然而这种扩张是以最终用户自由获取信息为代价的,颠覆了版权的利益平衡。”9支持这种观点的还有特蕾西?考德威尔(TraceyCaldwel),她在《数字时代的版权平衡》一文中,指出在数字化的技术条件下,私权扩张使版权的合理使用范围儿乎被吞没。版权的扩张限制了在合理使用制度下教育、科学、文学等创作者合法获得作品的自由。也有学者从法哲学的角度研究该问题,约翰?贝利(StrongBailey)和查尔斯(Charles)认为将所有权的基本理念错误地嫁接到版权制度上,才导致了今日版权的非理性扩张。出版商在“私权神圣”的理念支持下,其垄断权在不断得到财产权增加的刺激下不断扩大。也有学者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版权扩张的合理性问题。威廉?兰德斯(WilliamLandes)和理査德?波斯纳(RichardPosner)提出,外部拥挤是作品进入公有领域后社会价值减少的潜在原因。他们提出版权法应该调整、扩张,以确保版权人和公众的利益,以至于保证社会总体的经济价值。然而罗伯特?皮埃尔斯汀(RobertPiasentin)的《外部堋挤与版权扩张》却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数据库、地图和事实作品等并不会由于无限制使用造成外部拥挤而受损。而对于现有公共作品和版权作品的研究明,由于版权作品进入公有领域而导致作品需求下降是难以置信的。因此,“外部拥挤”不能构成扩大版权人权能的理论基础。
知识产权对信息权利限制问题
(一)合理使用原则数字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版权法的合理使用原则带来了挑战,有学者认为网络时代合理使用制度正面临边缘化的危机。由于技术措施的广泛使用与合法性的认定使权利人能够借助技术,对作品的使用权限进行控制,从而有效地避免侵权行为发生相应的,公众对作品的使用范围也由此缩窄。并且,即使仍然规定合理使用情形,但因技术措施的防护,公众在原有合理使用范围内对作品的使用权也会流于形式。原本排除在版权保护范围之外的作品以及数字、事实等原本不享有版权的内容,都会由于技术保护措施的应用,成为使用者获取这些资料的障碍。在纽约大学的布伦南司法研究中心公布的题为《合理使用能否幸存?版权控制时代的自由表达》(WiFairUseSurvive?FreeExpressionintheAgeofCopyrightControl)的报告中指出“合理使用和自由表达存在风险”,而解决的途径是“碱轻侵权行为的处罚,建立国家法律援助中心,提供代理律师,为所谓的非合理使用行为进行辩护”。从司法实践来看,合理使用原则在判断网络侵权行为中被法官屡屡使用。在aster案中就运用了传统版权保护中“合理使用”的四原则判定该公司是否侵犯了版权。2006年绕Google公司的两起诉讼,更引起了学者们对于“合理使用”怎样应用于判定数字侵权的争议。在Blakefield诉GoogleInc.案例中,原告认为Google将自己的文章收录至缓存系统并提供其用户搜索、找到该文章,侵犯了自已的版权。内华达州地方法院裁决Google公司未侵权,认为(google通过缓存链接方式提供享有版权作品的存取只是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功能,属于衍生性使用。同时由于该作者并未对作品进行加密限制,是免费提供给公众的,因此该作品并没有1个”销售市场”,那么Google的使用也未对该作品的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可见,在这个案例中,合理使用原则的运用使得“复制行为本身已经不足以构成侵权”。这就与传统版权理论产生了沖突。在传统的版权理论中,Google缓存系统的使用本身就是一种侵犯版权行为,由于它对作者的整篇文章在未获得许可的情况下进行了违法的复制。而在Google数字图书馆案中,Google认为,将馆藏置于可搜索的数字形式是种合理使用,由于该使用是基于学术目的的,Google不会从中直接获利,将享有版权的作品置人特殊的可搜索数据库中是一种衍生使用,该作品的可搜索性并不会对其销售产生负面影响,而对于享有版权的作品而言,用户通过搜索仅能看到链接到的作品中有限的几句话。出版商却认为:Google是1个商业实体,通过这个图书搜索服务Google是能够获利的,Google在建立数字图书馆时必须对整部作品进行扫描?仅仅将作品的传播介质进行转换(成为在线)也不能称作行生使用,而使用者在能够通过免费链接获得作品的情况下就不会再去购买该作品。但也有学者指出,该计划并没有威胁到出版商固有的核心市场,相反还起到了营销的作用。不过即便如此,出版商仍指出,Google向读者免费提供商业或潜在商业使用而没有给于出版者补偿同时也忽略了质量控制。Google数字图书馆案:2004年美国作家协会和美国出版商协会代表麦格劳、希尔集因、培生教育出版集因、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以及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对Google提起的版权诉讼,认为Google在未荻得版权许可的情况下,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密歌根大学的困书馆,组约公共图书馆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达成协议,将其所有馆藏数字化并向公众提供在线获取,严重侵犯了其著作权。在案件审理中,部分学者认为法院仍然很可能运用合理使用原则,由于使用目的和市场影响原则会让法官判定某些数字化使用构成合理使用,这样一来从实质上就扩大了合理使用的范围。对于出版商而言,Google提供给图书馆的数字拷贝将直接取代出版商或其代理商电子出版物的销售,而图书馆使用这些数字拷贝也不再受出版商许可证资质的制约,这一切无疑都削弱了对于权利人合法权利的保护。但也有学者发表不同的观点,认为”目前,合理使用是侵犯版权的1个抗辩,是作为1个平衡物来维持公众与私人之间的适度平衡。假如侵权问题不再被触及一一由于权利管理技术在侵害行为发生以前就将其阻止了一一那么合理使用问题就不会再出现”。(二)强制许可原则数字环境下,强制许可也受到了挑战,私人协商和集体许可管理规范逐步代替了原先的强制许可做法。并且,事实证明集体管理(CollectiveAdministration)的做法是成功的。在许多国家(如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印度、韩国、以色列、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以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集体管理组织既许可音乐作品的复制发行权,又许可公开表演权,因此给被许可人提供了更加有效率的站式销售”服务,也为版权人提供了流水线式的使用费处理服务。因此,2005年7月12日,在向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知识产权分会提出的报告中,美国版权申请注册官theRegisterofCopyright)MarybethPeters提出了修改版权法第115条的具体建议,围绕着数字音乐传输应该建立“一站式销售”模式提出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第1个方案是将第115条规定的强制许可进1步扩展到数字音乐传输,可是,要建立起与第114条音乐录音法定许可模式类似的“一揽子强制许可”(BlanketCompulsoryliCEnse),或者建立起与其他国家类似的集体管理规范,将第115条规定的强制许可扩大适用于公开表演行为。第2个方案是彻底废除第115条规定的强制许可,仅规定集体管理组织的集体许可(完全由市场自由协议来解决),或者干脆简单地废除该第115条就能够了。最终在正式的修改法案中,采用了第一种方案。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