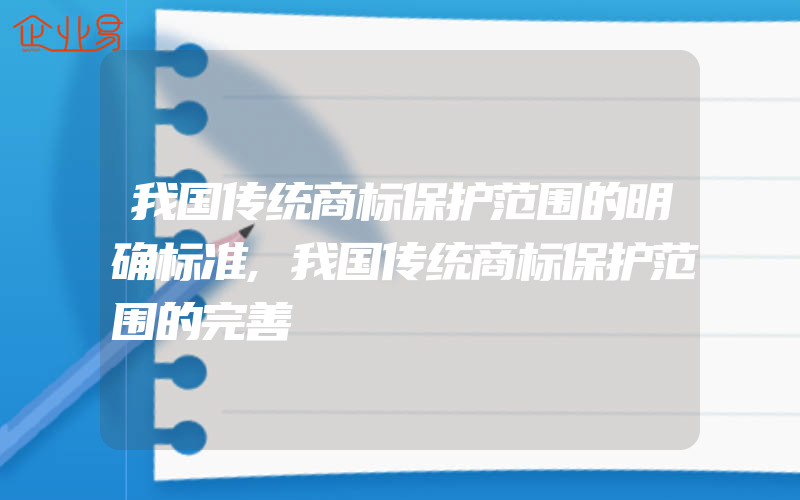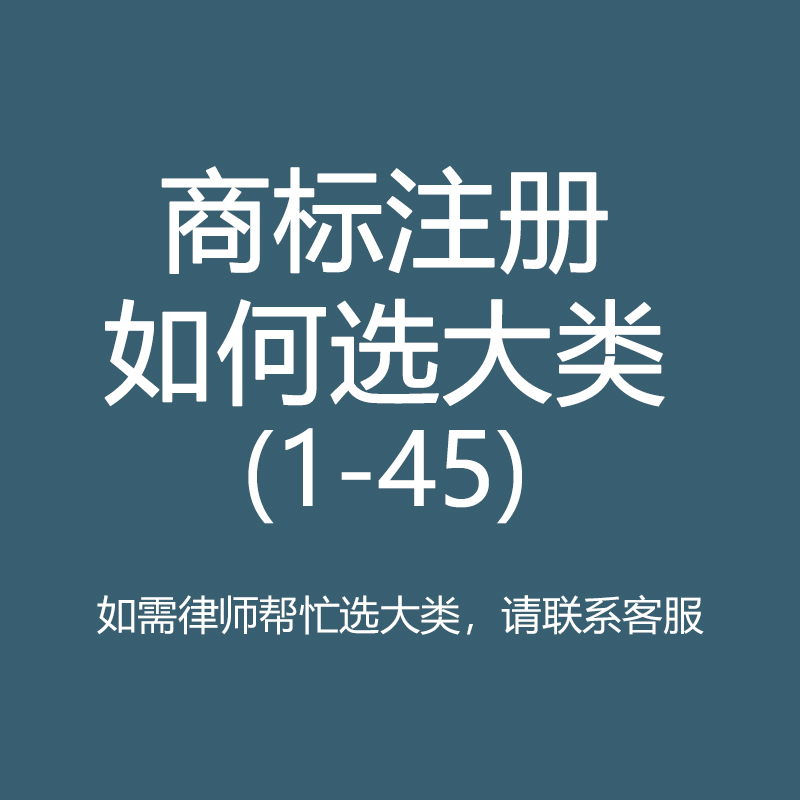我国传统商标保护范围的明确标准
我国《商标法》没有将混淆作为判定商标保护范围的标准,而《商标法实施条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侵权行为之判定则将混淆列为条件之一。就立法技术而言,“类似商品”、“近似商标”在用语上存在着与欧共体混淆理论相同的问题,此不赘言。此外,我国的标准还存在以下问题:1.《商标法》第52条存在明显缺陷《商标法》第52条就商标专用权的禁止范围只列举了商品相同或类似,以及商标相同或近似这两个条件,而没有将混淆可能性作为要件。就逻辑关系而言,商标、商品均相同是造成混淆的充分条件,但除此而外的其他三类情形(商品相同与商标近似;商品类似与商标相同;商品类似与商标近似)则未必是构成混淆的充分条件,假如一概认定为侵权,显然有悖于商标保护的基本原理。LG案就属于“商品相同、商标近似但不构成混淆”的代表性案例。该案中,原被告双方商标的使用商品同为电梯。原告申请注册商标(图1)与被告申请注册商标(图2)尚存在较大区别。可是,原告商标与被告实际使用商标(图3)难谓“不近似”:原告商标是“LG+图形”,被告实际使用商标只是“LG”,且两个“LG”在外观上区别甚微,消费者很可能认为后者是前者的系列商标,因此两者存在相当程度的近似。然而,假如承认这两个商标构成近似,则依据《商标法》第52条规定,就应认定被告使用行为构成侵权。可法院偏偏又觉得不应认定被告侵权。为此法官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分析两商标之间怎样存在区别,从而不构成近似商标。于是,判决书中就出现了这样的妙论:“原告商标中的L’、‘G’是汉语拼音字母的写法,发音是汉语拼音的发音”;“被告商标中的L、C’是英文字母的写法,发音是英文字母的发音”,因此,两商标文字部分“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字,尽管字母写法相同,但发音不同,因而,不应认为是相同”。该理由实属牵强,试问消费者怎样能就两商标中的“LG”区分出汉语拼音和英文字母的写法和读音?因此,两商标由于具有相同的字母构成和读音,应判定为近似商标。可是,消费者并不会因此发生混淆原因在于电梯“不是普通的日用品。电梯的消费者一般是单位,单位在购买安装电梯这类特殊商品的过程中,对所购买的电梯,包含电梯上使用的商标施加的注意力,要较普通消费者对普通日用品施加的注意力大得多”。笔者认为,法院关于相关消费者的注意力程度之考虑是恰当的,但对双方商标不近似的认定存有疑问。并不是消费者注意力高了,商标就不近似了,于是就不构成侵权;而是消费者注意力高了之后,即使商标存在近似之处,也不会发生混淆误认,自然就不构成侵权。当然,也许本案法官也看出了端倪,然而囿于现行立法的明文规定,不得不曲线救国而已。为了破解《商标法》第52条在司法适用中造成的难题,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将“商标近似”之判定与混淆结果相联络,认为应当结合是否导致消费者误认来判定商标是否近似容易造成误认的属于近似商标;不会造成误认的商标不构成近似。这种标准是将“近似”的概念替换为了“混淆性近似”的概念,从效果上修正了立法存在的问题。然而,这种做法仍然经不起推敲:(1)用混淆作为商标近似的判定条件在逻辑上存在缺陷:近似是混淆的原因,而不是相反。(2)导致法律用语同常识背离。依据上述“混淆性近似”理论,近似程度相当的两个商标可能在某一案件中被判定为近似,在另一案件中被判定为不近似,由于“就人民法院审理的具体的商标纠纷而言,仅有在存在‘混淆或者混淆的现实‘可能性’时,才能够判断商标近似”。这样就出现了法律上的近似与日常生活中的近似相分离的现象。已有学者指出了这个问题:“在商标“近似’与混滑’关系问题上,混淆”是‘近似’的前提。这一判断或许不符合人们的日常经验可是,离开了混淆这一前提,近似’就不具有法律意义。”(3)导致商标近似成为难以捉摸的问题,使所谓的近似判定标准丧失了“标准”的意义。例如,茅台集团申请申请注册的“茅台迎宾”商标与别人申请注册在先的“迎宾”商标不被判定为近似,但假如别人申请申请注册“迎宾茅台”则无疑会被判定为与茅台集团的“孝台”商标构成近似。其实,单纯从商标文字的音、形、意诸因素分析,“茅台迎宾”、迎宾”和“迎宾茅台”、“茅台”这两组商标在近似程度上是相同的。之因此前一组商标能够并存申请注册和使用,不是由于它们不近似,而是由于“茅台”的知名度太高,消费者只会将“茅台迎宾”与茅台集团发生联络,而不会将其与别人的“迎宾”商标相联络,也即不存在混淆的可能性。后一组商标不能并存申请注册和使用,也不仅仅由于它们构成近似,而是由于“茅台”的知名度太高消费者容易将“迎宾茅台”误认为是茅台集团的系列商标,也即存在混淆的可能性。总之,由于《商标法》没有将混淆作为商标传统保护范围的判定基础,尽管司法解释通过引入“混滑性近似”的概念加以修正,仍然难以弥补立法的缺陷,实践中只能以“个案原则”加以掩饰。出现越来越多适用个案原则的情况,实际上已经在提醒我们:可能是标准出了问题。2.《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和司法解释使用了不同的近似概念《商标法实施条例》及相关司法解释就申请注册商标与其他标志的冲突之处理规定,必须考察3个要件:(1)商品是否相同或类似;(2)商标与标志是否相同或近似;(3)是否造成相关公众混淆。从而,近似问题成为单独的要素不必须通过混淆的结果来反推。混淆的结果要依据商品的关系、商标与标志的关系以以及他环境因素来综合判断。能够看出,《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和司法解释对“近似”概念的使用是不统一的。《商标法》第52条的“近似”经过司法解释的修正实质上等于“混淆性近似”;其他侵权类型所用“近似”概念不受“混淆性”的限定,在外延上要宽于“混淆性近似”。3.对具有较强显著性或较高知名度的商标保护不力,造成传统的保护范围与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之间出现了空隙首先,商标的传统保护范围受限于固定化的商品类似关系。在商标、商品二因素判断中,商标的显著性或知名度是商标近似判断的参考因素,但与商品是否类似的判定无关。这样,强商标的保护范围只能在商标纬度上扩大,难以在商品纬度上扩展。商品类似关系是否存在个案原则,目前仍无定论。行政及司法程序中所谓的“个案原则”,实质只是对《区分表》所规定的商品类似群组的突破而非基于强商标强保护的原则加以突破。其次,即使在后商标使用在类似商品范围之外存在与在先商标相混淆的可能性,在先商标获得保护的可能性也极小。按照现行立法,类似商品之外就不属于传统的保护范围,应交由驰名商标特殊保护制度管辖。然而,启动该特殊制度的门槛极高,仅有很少的商标能够达到驰名的条件。这样,尚达不到驰名条件的知名商标只能任由别人在“非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即使这类行为误导了公众,在先权人也无能为力。须知,知名商标是任何驰名商标从普通商标到驰名商标的必经阶段。假如在知名阶段得不到强有力的保护,一些潜在的驰名商标就将天折,即使个别幸存者熬成了驰名商标,却已经没有扩大保护的必要了,由于在各类商品上都有别人申请注册相同近似商标且已不可争议。这种保护上的空隙迫使一些知名商标所有人不惜代价在所有类别上进行防御性申请注册,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使注册商标簿拥塞不堪。最后,尽管司法解释对混淆类似进行了扩大解释,认为混滑既包含来源误认,也包含与欧美赞助混淆相类似的“特定联络的误认”,可是,按照现行类似标准,在类似商品上假如消费者会有混滑,大部分就是对商品来源的混淆。因此,在商品类似关系被固定的情况下,特定关系的误认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的空间。
我国传统商标保护范围的完善
(一)对商标保护传统范围的思考笔者认为,商标保护的对象并不是商标的外部表现形式,而是作为三元结构整体的实质意义上的商标。仅有当商标在商业中实际使用之后,才能具备区分功能及质量保障功能和广告功能,才能凝聚商誉。这些功能所传达的信息使商标具有了降低消费者搜索成本和促使厂商维持及提高商品质量的效用。商标上述经济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同一商标所指示的商品来源具有唯一性。作为符号的商标外部表现形式不能通过占有而排斥别人的使用,假如缺少了法律的介人,上述唯一性就很可能由于别人的模仿或者偶然巧合而受到破坏,消费者就难以获得关于商品来源的正确倌息。在此意义上,“商标法的核心任务是促进正确的信息在市场上传输”。错误的来源信息容易导致消费者对商品来源或者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混淆。混淆既伤害了消费者又损害了生产经营者:混淆性或欺骗性的商标会误导消费者去购买其并不想要的商品,而生产经营者的销售或者商誉相应将受损。可是,假如竞争对手所使用的相同或近似商标并没有使消费者对商品来源或不同主体之间经济联络产生混淆,则不会损害消费者及在先商标权人的利益,在先商标权人就不能禁止竞争对手的使用。总之,消费者是否发生混淆或是否存在这种混淆的可能性就成为划定商标权传统范围的依据,据此明确的权利范围兼顾了在先商标权人、竞争对手和消费者三方的利益。(二)制度选择我们能够按照欧共体的模式对现行《商标法》进行改良,即按照商品关系和商标关系对侵权行为进行分类,并增加混淆及混淆可能性作为侵权行为的构成条件。但这并非上策,由于欧共体模式本身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笔者建议,我国商标法应明确采纳美国的混滑理论。我国部分法院已在司法实践中开始了对混淆理论的探索。例如,在山东创新科学技术公司诉青岛世元啤酒厂等商标纠纷案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出,“商标最基本的功能在于识别商品或服务的来源对申请注册商标予以保护,除基于保障申请注册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外,更为重要的在于避免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的来源造成误认,故制止混淆和混淆的可能为商标法的立法目的所在。……而判断是否会对申请注册商标专用权构成侵害,则以是否造成混滑或误认以至于误导公众或普通消费者为要件。换言之,即使所使用的标志与申请注册商标相近,但不足以造成混和误认,则不能认定为侵犯商标权行为。而判断是否会给公众或普通消费者造成混淆和误认,又因不同申请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差异而存在区别。商标的显著性越强,造成混淆的可能性越大。而显著性弱的商标,别人使用的标志即使与申请注册商标相近也难认定为混滑。而显著性的取得,除商标自身由于外观含义等因素而较为显著外,通过长期使用取得较高的知名度,并产生了识别商品的较强能力,亦能使商标取得显著性。总言之,对于申请注册商标的保护,在判断侵权所依据的标准上是一致的但在保护范围上却又因商标而异”。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