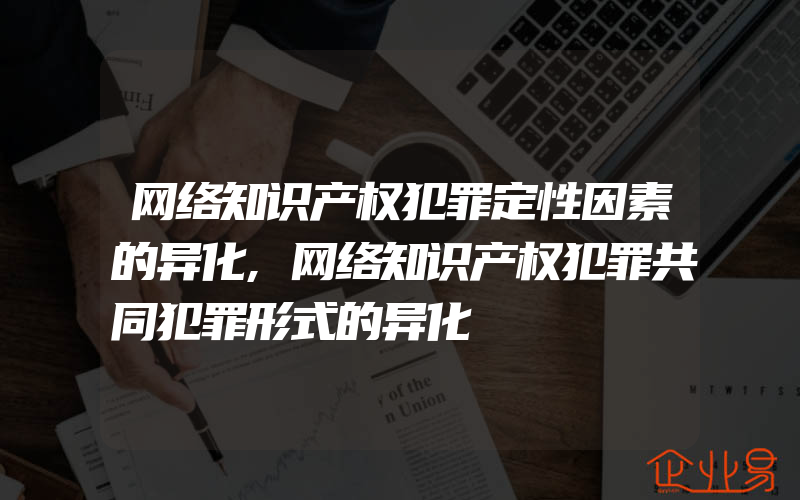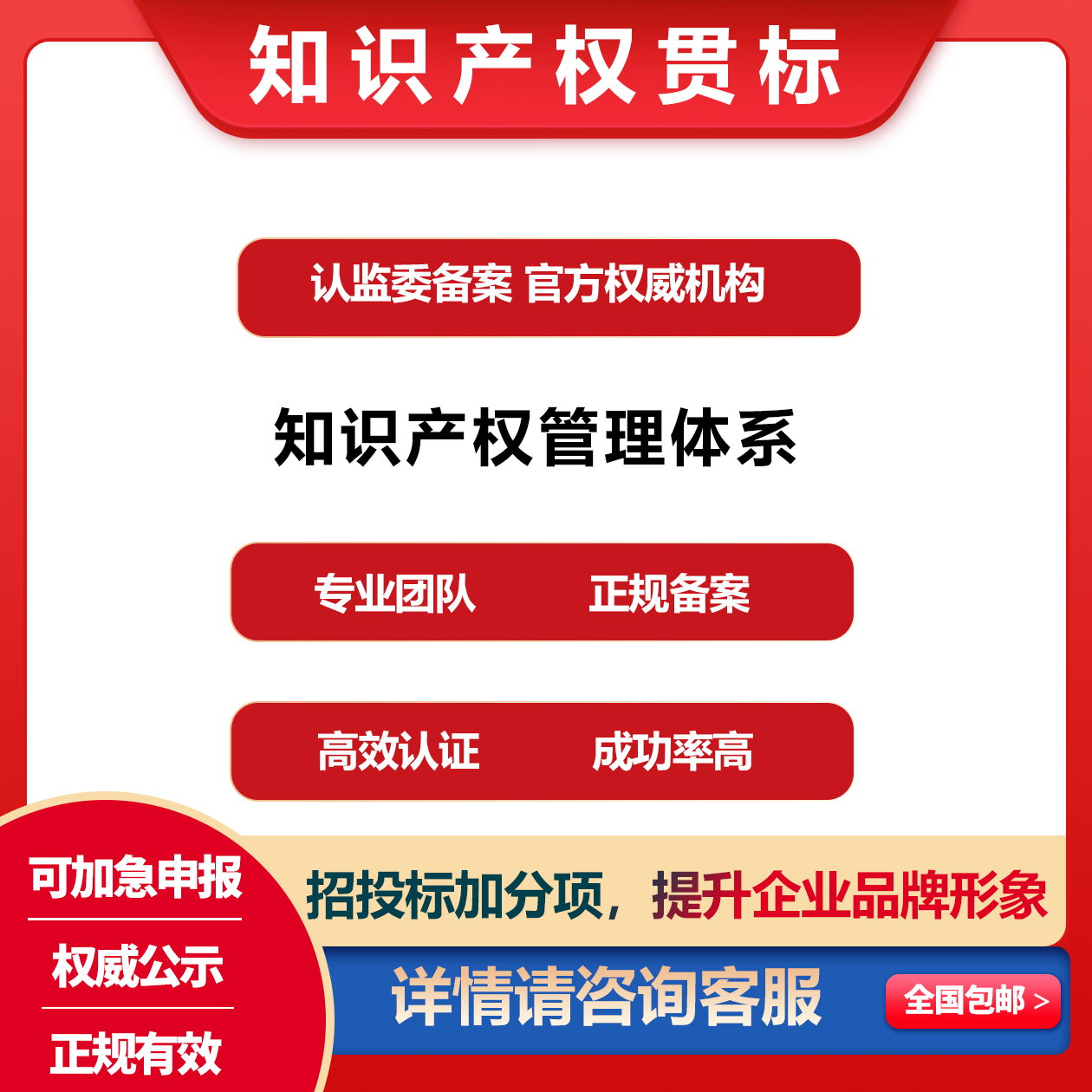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定性因素的异化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重要性凸显。近些年我国加强了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然而,在对知识产权犯罪进行打击时,往往会受到传统知识产权犯罪的网络异化的冲击。2006年公安机关在打击知识产权犯罪专项行动的总结中就明确指出“犯罪在网络上发生异化,传统立法难以与网络犯罪相适应”是目前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主要困难之一。(1犯罪是1个动态的现象,随着外部环境的转变而转变,网络犯罪亦随着网络更新换代不断的发展转变。早期的网络犯罪中,犯罪的对象主要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本身,而在“网络2.0时代”,网络平台和生活平台相互交织,现实社会的传统权益延伸到网络空间,网络犯罪开始转向传统法益,传统犯罪的网络异化成为网络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而这也同样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主要发展趋势。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定性因素的异化网络具有虚拟性和技术性的特性,网络空间中信息传输的便捷是现实社会无法比拟的,传统犯罪在同网络特性相结合后,部分传统犯罪在行为方式上会产生异化,导致传统刑法规则的评价困难,难以通过刑法对其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予以认定,即在犯罪的定性因素上产生了异化。而在知识产权犯罪之中,由于知识产权的智慧财产的特性同网络特性的契合,这种异化则更加明显。以侵犯著作权罪为例,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别人作品是犯罪的行为方式之一,在传统社会中复制和发行都不难理解,由于现实社会的作品必须依托于书籍、光盘等物质载体,复制、发行实质上是对物质载体的复制、发行,可是当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发生在网络空间之时,其行为能否视为传统的复制、发行则产生了争议。尽管通过相关的司法解释,最高司法机关提出信息网络中的传播行为能够视为侵犯著作权罪的“复制发行”,可是,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实际上仍未能解决,例如,将纸质作品通过扫描等方式数字化的是否属于复制?将数字化作品信息在互联网中有限传播的是否属于发行?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知识产权的复制权、发行权和新型知识产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之间的关系的认定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属于新型权益,应当对其进行独立的保护,欧盟的《版权指令草案》和日本对著作权法的修订,都体现了此种理念,1而从我国《著作权法》等法律规定来看,我国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实质上也将信息网络传播权视为同复制权、发行权的独立杈利类型。而假如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不同于复制杈、发行杈,那么由于侵犯著作权罪中,未能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作为客观行为方式之一,对于此类行为能否定性为侵犯著作权罪显然会让司法机关进退两难。
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共同犯罪形式的异化
知识产权犯罪的网络异化是全面的,异化不仅体现在单独犯罪层面,知识产权共同犯罪同样在网络空间产生了异化,无论是客观的共同的犯罪行为还是主观的共同犯罪故意,都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知识产权共同犯罪的新特征,给传统的共同犯罪刑法理论带来冲击的同时,更是给司法实践认定带来了困难。1.共同犯罪行为的网络异化共同犯罪行为是成立共同犯罪的客观基础,传统共同犯罪行为体系中,实行行为处于核心地位,实行行为的性质决定了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实行行为的实施者大部分情况下都属于主犯,而常见的协助行为则处于从属地位,依托于实行行为,协助行为的实施者多数情况下被认定为从犯。然而,在网络知识产权共同犯罪中,传统的共同犯罪行为认定规则被打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网络犯罪的技术性,技术性的支持行为在网络空间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提供技术协助的协助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重要性逐渐超越实行行为人。早期的网络犯罪,犯罪人普遍掌握高超的网络技术,目前的网络犯罪尽管已然“平民化但并不是由于网络犯罪的技术性要求降低了,而是由于网络空间中获得技术协助更加便捷了,技术性支持行为依旧在网络共同犯罪中处于关键地位。例如,目前的计算机软件在理论上都能够被无限复制和传播,可是由于计算机软件上附着的技术措施阻止了非法的复制,犯罪人想复制发行含有盜版软件的光盘,首先要获得技术协助,能够破解技术措施,一旦技术措施被破坏,随后的复制软件的行为就极为简单了。能否破解技术措施这一行为成了复制、发行盜版软件的关键,提供破解技术措施协助的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当被视为主犯。二是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信息交流的便捷性,改变了协助行为的行为模式,网络空间中协助行为所呈现出的“一对多”的协助模式,急剧放大协助行为危害性的同时,还带来了行为定性的困难。传统社会中,受限于时间和空间,协助行为人在定时间内往往只能为特定的1个犯罪实行行为提供协助,然而网络空间打破了空间和地域的限制,使在同一时间对多人提供协助行为成为可能,例如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1个网络平台,能够同时协助多个行为人实施销售盜版软件,网络服务提供商轻易实现了同时协助多个独立的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行为,可是对于网络服务提供商行为的定性则存在着困难。提供网络平台的行为实质上属于侵害著作权实行行为的协助行为,其定性依托于实行行为,当实行行为不成立犯罪时,协助行为自然也不成立犯罪。因此,在提供“一对多”协助的情形下,很可能会出现协助多人,造成了严重影响,可是由于被协助的每1个实行行为实施者都未达到犯罪定量标准,而难以作为犯罪处置的情形,放纵了此类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协助行为。2.共同犯罪故意的网络异化网络知识产权共同犯罪的异化还表现为共同犯罪的主观方面上。传统共同犯罪理论要求,共同犯罪人在主观上有意思联络,并且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然而,网络知识产权共同犯罪的行为人之间,主观上往往不具有意思联络,网络的虚拟环境下,网络参与主体的身份都是虚拟的,以上文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协助行为为例,网络服务提供商和利用其服务侵害别人知识产权的行为人之间,往往不具有任何联络,网络服务商只是提供了1个平台,任何人都能够使用。在缺乏主观意思联络的情况下,认定共同犯罪显然同传统刑法理论存在冲突,然而假如不认定共同犯罪成立,缺乏了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行为怎样去界定网络服务商的行为性质?这无疑又是1个司法难题,刑事立法和司法未能有效对其进行回应,客观上造成了大量在网络空间中为别人侵害知识产权提供协助的行为,尽管已经具有明显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且实质上是网络空间中侵害知识产权行为存在的主要因素之一,可是却无法受到刑法的制裁,客观上放纵了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削弱了网络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效果。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