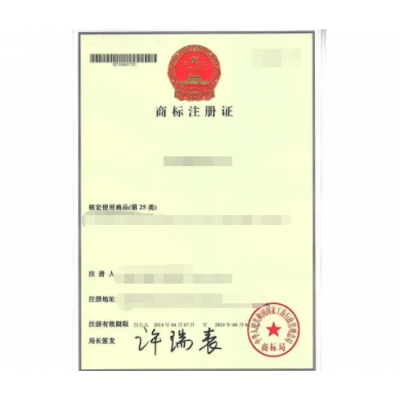我们欲图管中窥豹,揭示司法实践中对“商标淡化”的基本理解。在1个成文法的国度,既决案例对于类似案件并无当然的法律效力,因此这样一种分析统计方法,不管是怎样精确,其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能昭示司法现实,本身始终是1个问题。尽管方法未必恰当,结论也不可避免具有片面性,可是这种不成熟的研究方法对于了解司法实践的真实情况,了解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的思考方式及推论方法,多少有些协助。本节本意是希望尽量客观呈现司法实践中的“商标淡化”纠纷以及法官对该类问题的应对,但在案例的分析和研究中不可避免地扩大到商标的含义,商品是否类似的认定,《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商标法》之间的关系,等等与之相关的问题,并且引发评议。尽管本节将淡化纠纷的类型分成四类,但第四类是1个特殊的概括性分类,实际上包罗万象。司法实践中淡化理论的运用范围之广,远出乎作者初始的想象。关于法律依据中国司法实践中应对商标“淡化”纠纷,法律依据基本集中在两个条款中:一是《商标法》第52条第5项,或由其延伸出来的法释,例如在本节研究的第一类纠纷、第二类纠纷和第三类纠纷中,这种适用是主流;二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第2条,也就是有名的兜底条款。例如在本节研究的第四类纠纷中,这类适用成为主流。在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之下,前者的适用与传统的混淆理论融合在一起。这种意义下的“淡化”实际上是在混淆理论下寄居的“淡化”理论。导致以下观点成为必然:第一,认为商标淡化是一种侵犯商标权行为;第二,认为同等商品之间也存在淡化;第三,淡化与混淆难以区分。在美国商标淡化的发展史上,也曾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法庭对于淡化持消极的对抗态度,多借助扩大的混淆理论来实施淡化保护。Schechter早年力倡的淡化保护,即在“非竞争性”产品上,在非同类产品上的保护,借助赞助混淆、关联混淆等扩大的混淆理论得以涵盖。但这样的一种做法容易导致这样的理解:即混淆与淡化不分彼此,淡化侵权没有单独立法的必要,将传统的混淆理论扩大就足以应对商标淡化问题。而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来应对的商标淡化,其形态又过于丰富,其范围过于宽泛,边界难以预测。事实上,在第四类的纠纷中,已经涉及形象权、商业外观、商品标记等的淡化保护问题。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本身即为弹性条款的情况下,“商标淡化”这个术语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已经成为弥补法律漏洞的1个手段。但这一术语的运用同样可能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的另一极端。对商标淡化的这两种不同理解,在中国司法实践中非常独特地并行在一起。一方面,它使得商标淡化概念内部存在紧张对立关系,即到底是否存在独立于混淆之外的商标淡化成为1个问题;而此外一方面,假如将淡化归结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之下的一类独特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又使得法官在案件裁断的过程中具有相当大的弹性空间。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