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设权模式和行为法模式在基本范式和规范供给范围上的差异决定了只能将非驰名未申请注册商标所有人的禁止权设置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其根本原因在于未经申请注册或驰名的商标权益缺乏社会典型公开性,因此其权利归属效能无法彰显,自然也不应当赋予其强大的排除效能。这代表着在保护未申请注册商标权益时无法从侵害结果直接“征引”出违法性,而必须考察行为本身是否违法,(有关权利的“归属效能”“排除效能”与“社会典型公开性”之间的关系,参见于飞:《论德国侵权法中的“框架权”》,载《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2期,第69-76页。)也就是两类模式的分水岭。质言之,从正面看,市场竞争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存在“合法权利”“正当竞争利益”和法律放任的自由竞争”3个领域,三者内蕴的法秩序有所不同,靠前领域相较靠后领域,法律规范的介入更加积极。第一,合法权利对应设权模式:利益不再保持中性,破坏其完满状态的行为必然不正当,因此,法律救济的前提是证立被请求保护的利益符合法律预先设定的权利构成要件。第二,正当竞争利益对应行为法模式:保持利益中性,其立足点不是预先规定的静态权利,而在明确行为不正当性的基础上主张“禁止使用”。(参见孔祥俊:《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本范式》,载《法学家》2018年第1期,第5758页)第三,尽管自由竞争行为必然附带对其他市场主体的损害,却不能获得法律救济。能够看到,两种保护模式俱因涉及正当性批判而在原始意义上有同源的可能,可是二者批判对象不同:一为静态利益,一为动态行为。显然,理想中商标权的实质是经过针对商誉的正当性批判后成立的合法权利,其最终目标是合法利益的正确归属。(这只是理想中的完整商标权,前文已经述及商标法必须通过使用强制要求促成理想商标权的实现,此时完成了“保护商标权人”“保护消费者利益”“确保市场竞争秩序”3个立法目的的融合。)而未申请注册商标利益是中性的,对其造成的损害并不必然具有可救济性,能否主张“禁止使用”,以针对使用行为的正当性批判为前提从反面看,未申请注册商标上成立的禁止使用请求权不能以所谓有限的“相对权保护”为由而设置在商标法中。有观点认为,为了防止对申请注册制产生冲击,《商标法》第15条第1款的禁止权是囿于特殊关系的债权性“相对权”保护以此证明该禁止权的合理性。(王太平:《我国未申请注册商标保护制度的体系化解释》,载《法学》2018年第8期,第145页。)这种观点的含混之处在于既希望证立代理或代表关系的特殊性应当关联更加严苛的法律后果(禁止使用),又希望消弭这种“相对性禁止权”对申请注册制的冲击。然而,这种“两头讨好”的意图实则难以成立。由于请求权必然针对特定人,这里的“相对性”指的不是禁止使用请求权本身的相对性。因此该观点的实质是商标法同时基于两种关系提供“禁止使用”请求权:特定主体之间的相对关系、标的商标权)与主体之间的归属关系,(两类关系参见[德]梅迪库斯著:《请求权基础》,陈卫佐等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以下。)前者是债权性的本权请求权,后者是基于类物权的原权请求权。(各类请求权的区分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参见杨立新、曹艳春:《论民事权利保护的请求权体系以及内部关系》,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566页。)可是,商标法无法容纳前者。如前所述,在商标法秉持的设权模式下,提出特定请求的前提是判断某项事实是否符合预先设定的权利之定义,该判断过程体现为商标权的取得。除非承认所谓“未申请注册商标权”,否则只能依行为法模式从行为不正当的角度提出禁止使用请求。因此,所谓“相对性禁止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申请注册制的抵触,违背了商标法请求权体系的基础逻辑,并不会因其数量稀少或针对特定人而具备合理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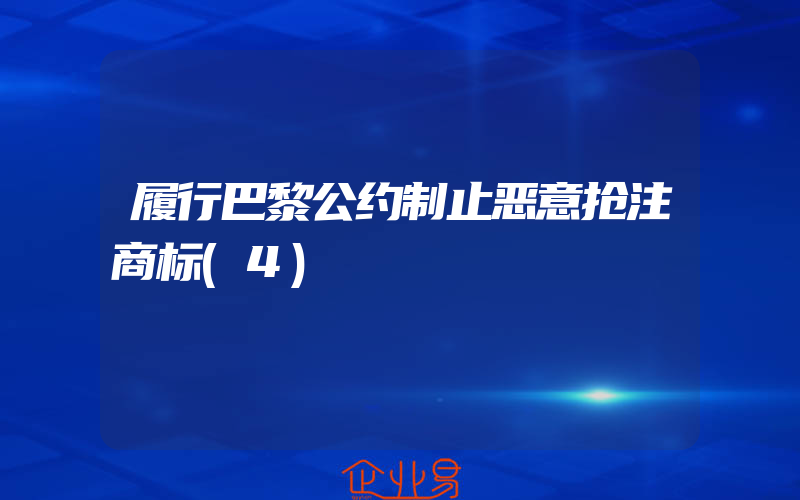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