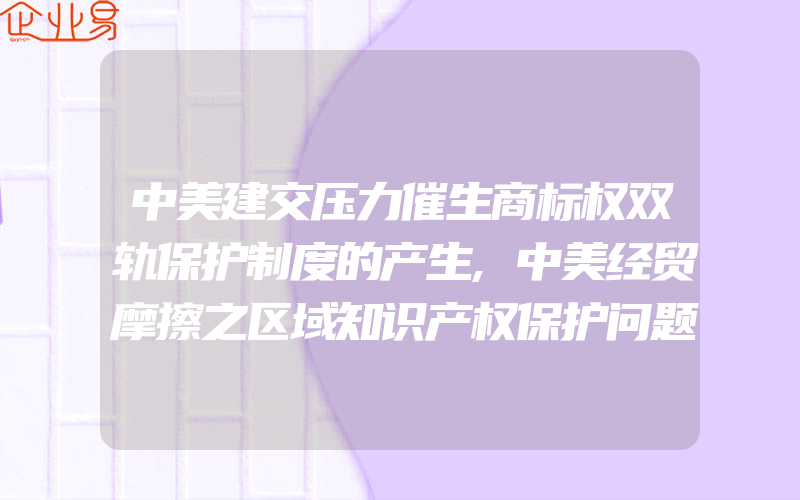中美建交压力催生商标权双轨保护制度的产生
“WHDGM”以后,由于我国经济的腾飞、国际交流的增长和对外贸易的增多,中国与外界的联络越来越紧密,此时在国际交往中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发达国家重视,而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欠缺显然成了交往过程中的一大障碍,因而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谈判,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日益被提上日程来。中国首次在协议中对知识产权问题作出承诺是在1979年中美双方签订的《中美高能物理协议》中。当时中国代表团由邓小平率领,对美国进行访问,双方在签署协议时,美方代表执意要求加入版权保护条款,当时中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法制和意识均未建立,对美方的坚持不甚理解,但考虑到谈判的目的主要是尽快与美国建立贸易关系,发展中国国内经济,扭转“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经济的颓势,中方代表很快就接受了美方的建议,在双方协议中加入了这一内容,并将其列为原则性的第六条款。此时中美关系正处于蜜月期,当年7月,为促进两国贸易关系发展,美国代表团访中,就促进双方贸易关系问题进行了谈判,在这次谈判中中国第二次被要求在协议中对国内知识产权问题作出承诺,有上一次协议的借鉴,这一要求最终再次被中方代表所接受,并由双方在该协议第六条款中作出五项承诺。不难看出,在上述两次中美贸易谈判中,对于美方要求的知识产权条款,我国均未标明质疑与反对,接受了美国代表的要求。这其中既与当时中国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急需通过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改革国内经济,发展生产力有关,也与当时我国经济发展落后,法制不健全,国内知识产权问题尚未成长为经济发展趋势有关。认识的欠缺和迅速发展国内经济的迫切愿望,使得在这两次中美谈判中,中方几乎全部接受了美方关于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建议条款。从此中国知识产权制度渐渐在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下,走上了法制化之路。为了使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尽快完善并与国际接轨,以履行与美国所签之协议,在国际方面,我国于1980年正式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成员国,1984年成为《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缔约国;在国内,于1982年通过了《商标法》,并在当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通过了《专利法》,初步建立了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全国法院系统并没有做好应对知识产权民事诉讼工作的准备,企业之间的纠纷还主要是依靠行政管理机关和行业主管机关的协调与处理。因此,在当时颁布的知识产权领域立法中,都不约而同地将对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制度规定于其中,采用行政手段来保护本来应当属于民事领域的私权。自1979年中美建交后,在全面建立与美欧发达国家贸易关系、履行协议义务及国内经济、科技快速发展需求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知识产权制度不断得到推进和完善。1982年《商标法》确立的商标权双轨保护制度,在当时条件下迅速实现了对商标权的有效保护,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中美经贸摩擦之区域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1.1文献综述针对中美经贸摩擦的知识产权问题,国内学者主要从国家宏观应对策略、战略制定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如陈继勇提出冷静分析目的和实质、科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及不断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执法力度[4];张守文提出完善相应法律法规[5];易继明提出全盘考虑、稳住阵脚、力挺多边机制[6];马治国提出大力推进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完善[7];曹新明等提出以翔实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维权[8]。在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定量研究方面,国外学者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国家层面的立法评价,而对执法状况及国内具体区域评价的关注有限。Rapp等通过立法分析的方式对159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进行了评价,形成R-R指数[9]。Ginarte等在R-R指数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正完善,创设了G-P指数,具体指标选取了立法中的专利客体范围、保护期限[10]。Sherwood搜集了相关领域专业人员的意见,并以此为基础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进行评价[11]。Kondo选用国家立法评价和问卷调查两部分进行了综合评价,指标选取方面也主要是专利保护范围、期限[12]。Ostergard意识到前人研究中对执法评价的缺乏,构建了涵盖国家立法情况与执法力度的量度方法,其中,执法方面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经济和贸易活动的国家报告》为基础构建了执法编码表[13]。国内学者以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或水平的研究居多,韩玉雄等在G-P指数的基础上增加执法力度评价[14];许春明等提出的具体度量指标在与韩玉雄等选取的律师占比、立法时间、人均GDP及WTO成员国一致的基础上增加了成人识字率[15];董雪兵等对许春明等构建的执法强度指数进行了标准化[16];詹映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指数构建了知识产权执法力度衡量指标[17]。部分学者关注到中国各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差异巨大,即使在全国统一立法的基础上,各地区执行也存在客观差异,于是,近些年关于区域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的研究渐次增多。其中,部分学者直接适用国家评价指标来进行区域测定,许春明等根据国家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体系以及度量方法,进行了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强度的测定[15];唐保庆等直接适用韩玉雄等设计的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度量指标[18];康继军等对董雪兵等的指标选取进行了相应地方化处理[19]。在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其他具体领域的相互影响时,部分学者选择个别指标代替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如李梅等选用知识产权侵权结案率[20],李莉等选用技术转让市场规模[21],靳巧花等则将两者结合[22]。区域问题专门研究中,知识产权综合评价较多,如王黎萤等构建了区域知识产权制度实施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针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指标有4项[23];任婉竹等构建了区域知识产权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指标设两个二级指标[24];赵喜仓界定了区域知识产权保护能力的概念,并以创造、运用两部分为基础构建了区域知识产权保护能力评价指标体系[25]。向征等针对区域知识产权保护能力进行了专门评价,认为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包含立法保护能力、执法保护能力和影响能力,并针对省域知识产权保护能力选取了10个量化指标[26]。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存在以下几个限制:第一,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衡量指标对区域不具有针对性。第二,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中涉及保护指标的设计,一般选取个别指标刻画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综合评价力较弱。第三,在指标和变量的选择上尚有不完善之处,部分执法指标与立法指标混淆使用;未能将知识产权的全面信息涵盖,如缺乏著作权、商标权等信息;指标和权重的明确多使用主观分析法,客观性不足。第四,未把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产权系统的关系阐述清楚,忽视了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等方面的指标贡献分析,也未明确具体占比。1.2中美经贸摩擦的知识产权原因第6次美对华“301调查”,实际矛头指向了“中国制造2025”,尤其关注中国电动汽车等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从美国启动仅需其单方认为有损国内利益即可进行的301(b)程序,以及中国知识产权制度不存在违背国际条约、规则能够看出,美国发动此次贸易摩擦具有战略目的。但中美经贸摩擦确实以知识产权之名开启,且寻知识产权问题之实,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手段限制中国创新发展。究其原因,美国作为研究开发密集型产业与高科技产品领域的世界领先者,对其他国家是否存在侵害知识产权和其他不公平技术转移情况十分敏感与担忧,他们认为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不好将削弱美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的公平竞争能力,这也在特朗普总统备忘录中得到说明[1];此外,近些年中国科技创新高速发展、在专利申请方面已经位列世界第1位,美国认为中国高速崛起存在不正当之嫌,在现实层面存在盗取商业秘密、侵犯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等行为,在制度层面缺乏有效解决知识产权侵权救济障碍的措施,将影响美国出口计划及可能剥夺美国公民在创新发展领域获得公平报酬的机会。1.3区域知识产权保护问题《2017特别301报告》指出,中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商业秘密保护不足、假冒商品的制造和销售泛滥,并且在部分领域外国主体准入市场存在限制,并归咎于知识产权立法不严、地方执法的保护主义,以及司法保护的区域不均衡等问题。《2019特别301报告》相较《2017特别301报告》,着重强调了知识产权刑事保护问题,包含刑事执法门槛过高、损害赔偿金过低等。总结之下,许多问题的产生均源于地方立法、执法、司法,如部分省(区、市)在地方立法中规定适用主体须是本地申请注册的企业、社会团体,具有本地户籍并在本地工作、学习的个人等,导致部分国外企业或个人相关申请渠道无法畅通;区域执法中,部分地区为短期保护地方经济存在执法懈怠行为,部分行政部门对当事人投诉举报不予回应,部门之间互相推诿;区域司法保护方面则存在司法不均衡、区域司法审判参差不齐问题,部分地区知识产权法庭审判工作开展迟滞。地域广阔、行政区域繁多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合力由各地区保护实际共同形成,而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大、特色各异、需求多样,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最适强度也各不相同,相较全国推行统一标准改革,地方问题自查先行改革创新也是一条可探之路。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