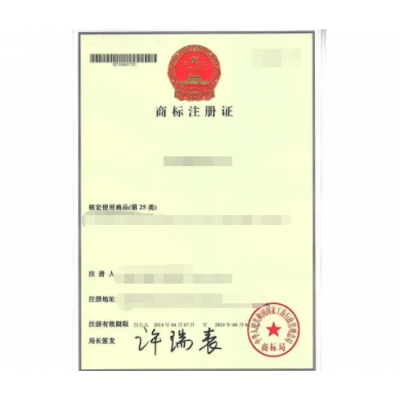我国商标保护模式与我国司法实践相脱节
我国以商标标识和使用的商品类别是否相同或近似作为判断侵犯商标权的标准,在个案审判中甚至已经完全被弃之一旁,而以混淆可能性取而代之。例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05年年底审结的“陈永祥与成都统一企业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侵犯商标权纠纷案”中,陈永祥享有“老坛子”申请注册商标专用权核定使用商品为29类,包含泡菜、酸菜、腌制蔬菜、咸菜、榨菜、腐乳、蔬菜汤料等。商标为一坛子的正面视图,下有“老坛子”3个中文字,坛子中间为“LAOTANZI”拼音。统一企业在其生产的方便面产品“统一巧面馆老坛酸菜牛肉面”的包装袋内配有一调味包。调味包内的实物为酸菜。调味包的包装袋上印有坛子的正面半身视图,图下印有“老坛酸菜风味包”几个由大至小的字,调味包左上角印有统一企业的图形与英文组合商标。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调味包作为方便面的配料,虽不单独销售,但随方便面一起进入流通领域进行交易,具有使用价值,并能产生价值,具有商品的属性。消费者食用方便面的情况下,存在着区分调味料生产者的可能性,因此调味包应该是种商品。酸菜调味包上作装潢使用的坛子图形和“老坛”文字,与陈永祥拥有的“老坛子”图文商标相似,并且使用在同一类商品上。可是,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将与申请注册商标相似的图文作装潢使用是否构成侵犯商标权的前提是足以使消费者引起误认。商标的主要功能是区分商品的来源。假如相关消费者在购买或使用统一企业的“老坛酸菜牛肉面”时不会将其与使用了陈永祥的“老坛子”申请注册商标的商品相混淆,则侵权不成立。在本案中,调味包虽是商品或商品的一部分,但密封在包装袋内,在消费者选购商品时不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消费者在使用商品的情况下,打开外包装袋后会看见酸菜调味包,这时必须结合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来考察消费者在使用该酸菜调味包时会不会误认为是陈永祥生产的或陈永祥许可生产的产品。就显著性而言,“老坛子”虽不是泡菜等商品的通用名称或直接标明其功能用途,但坛子是制作泡菜的传统工具,西南地区的群众习惯将陈年泡菜称为老坛泡菜。因此,“老坛子”用以指示特定泡菜生产者的功能较弱,显著性不强。就知名度而言,陈永祥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与统一企业发生纠纷前确已将“老坛子”商标实际进行商业性使用,并且通过使用获得了一定的市场认同。统一企业生产的方便面产品知名度较高,并且将坛子图形和“老坛”文字用于装潢方便面产品的时间早于陈永祥的“老坛子”商标的申请注册时间,一般消费者将统一企业的酸菜调味包误认为是陈永祥生产的或陈永祥许可生产的产品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据此认为,统一企业虽在相同的酸菜商品上将与陈永祥的“老坛子”商标相似的图文做包装装潢使用,但尚不足以使一般消费者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因此不构成对陈永祥的“老坛子”商标专用权的侵犯。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中的思路已经体现得很清楚即使被告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图形和文字都很近似的商标,假如不足以使普通消费者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就不应当认定构成侵犯商标权。也就是说,即使符合我国《商标法》第52条规定的“未经注册商标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申请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只要不存在混淆的可能性,就不构成侵犯商标权,或者说,是否存在混淆的可能性才是判断侵权与否的标准,“未经注册商标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申请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仅仅是认定是否存在混淆可能性的1个参考因素。
我国商标保护模式与我国司法实践相脱节
我国商标保护模式与我国司法实践相脱节我国《商标法》这种保护商标标识而非防止消费者混淆可能性之立法规定,被我国司法实务界采取各种不同的措施来规避。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解释中,已经将是否导致消费者混淆的可能性,作为判断商标及商标使用的商品或服务是否近似的标准。例如,在解释《商标法》第52条第1项规定的商标近似时,认为“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申请注册商标相比较,其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合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申请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络”,《商标法》第52条第1项规定的类似商品,是指“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般认为其存在特定联络、容易造成混淆的商品”,“类似服务”,是指“在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般认为存在特定联络、容易造成混淆的服务”,“商品与服务类似”,是指“商品和服务之间存在特定联络,容易使相关公众混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用是否容易造成相关公众混淆来解释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体现得更明显。在解答“怎样判断商品与服务是否类似”时,认为判断商品与服务是否类似应考虑下列因素:商品与服务在性质上的相关程度,在用途、用户、通常效用、销售渠道及销售习惯等方面的一致性,即在商品和服务中使用相同或者近似商标,是否足以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甚至明确指出“足以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是构成商标近似的必要条件。仅商标文字、图案近似,但不足以造成相关公众混淆、误认的,不构成商标近似,在商标近似判断中应当对是否足以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进行认定。”假如将我国这些司法解释与国外立法相比较,就会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其他国家是将商标和商标使用的商品或服务是否相同或近似,作为分析是否存在混淆可能性的条件;而我国则是将是否存在混淆的可能性,作为商标标识是否近似、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的判断标准。这也反映了我国司法实务界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混淆可能性才是真正判断侵犯商标权的标准,只不过碍于我国《商标法》没有采纳混淆可能性之判断标准,而是以商标标识和商品或服务是否相同或近似作为判断标准,假如直接采取国际上通行的侵犯商标权认定标准,将商标和商品或服务的相同或近似作为分析是否构成混淆可能性的标准,将有知识产权法官造法”之嫌。(崔国斌:“知识产权法官造法批判”,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而将混淆可能性作为认定商标是否近似、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则能够最终实现将混淆可能性作为侵犯商标权标准的目的。我国司法界利用混淆可能性来界定商标标识和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采用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策略,是一项高明之举,也是一种无奈之计!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