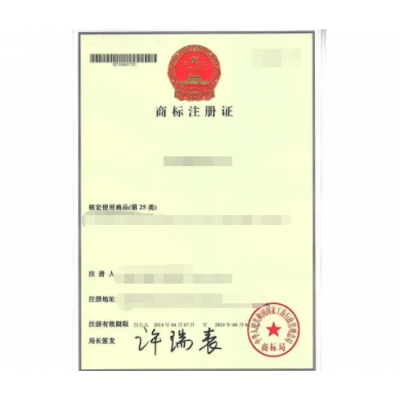商标权限制应成为商标法不可或缺的内容
竞争法范畴意义研究商标权,代表着商标权的实质是对别人行为的控制权,而不是对符号的垄断权。对别人行为的控制体现了竞争法范畴下商标法对竞争行为的规范功能和引导功能。商标法通过对商标权的保护和对违法者的制裁规范了竞争行为。同时,由于商标的资本性,使商标权的扩张可能违背竞争政策,产生反竞争意义。商标法必须通过内部机制的构建以实现对竞争行为的引导功能,将经营者使用商标的行为引向良性竞争。商标法的引导功能决定应对商标权进行限制以防止其反竞争意义的产生,使关于商标权的制度设计始终围绕实现竞争政策功能而服务。从这一意义上说,商标权是一种生而受限制的权利。这种限制的实质是通过法律对经营者的行为实施控制。?方面,商标应防止被仿冒,由于其关涉到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已达成的识别系统是否保持畅通;另一方面,商标应由商标权人正确使用,由于商标权实际上是一种商标利益的分配机制这一机制以恪守利益平衡原理为美德,一旦商标权被滥用,这种平衡将被打破。能够看出,商标法对商标权的限制是双向的。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对非商标权人的限制,由此产生了商标权的垄断属性,垄断是财产权的一般特征;后者是对商标权人本身的限制,其目的是淡化商标权的垄断属性,使商标权具有竞争政策工具的意义。有观点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是扬与抑的关系。所谓“扬”,即弥补知识产权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所谓“抑”,即限制知识产权领域的违背竞争法精神的滥用行为。事实上,商标法也是一种扬与抑的关系,“扬即确立商标权的垄断权,¨抑”即通过制度本身抑制商标权有悖竞争法理的不恰当行使。商标权是一种制止不正当竞争的权利,赋予商标权是对别人假冒行为的限制,同时商标权作为一种行为控制权,且对于垄断权,本身也有被滥用成为不正当竞争手段的危险,因此商标权的行使也是竞争法规制的范畴。在竞争法视阈下研究商标权及商标法,将商标法纳人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体系中,会发现对于商标领域的不正当竞争应从两个方面来规制:一是对于别人利用商标权人的商标从事假冒行为的不正当竞争应予规制;二是对于商标权人本人利用商标权而进行的不正当竞争同样也应予规制。对这两个方面加以规制,既是保持商标权财产概念完整性的必须,也是体现商标权竞争政策内涵的必须。这是由于,作为商标使用的文字本身是一种公共资源。当这种符号被赋予特定含义—与商品或服务建立了固定联络后便成为商标所有者的一种专有权。但这种专有权与有形财产的专有毕竟不同,它缺乏物理形式和空间占有,实质上是人们意念中被赋予的权利或称拟制财产,因此其专有性当然是相对的、有限的,只在标识商品和服务来源这特定语境下存在。在其他语境下,作为商标使用的标识只具有符号意义而不具有财产意义。从财产的角度,有必要对作为商标使用的标识的垄断权作个范围上的明晰,以此区别公有和私有的边界。从促进竞争的角度,商标法作为制止混淆的激励机制,它赋予了商标权人禁止别人利用商标进行不正当竞争的权利,这种权利实质上是种行为控制的权利。不正当竞争与正当竞争是相对而言的。所谓不正当竞争,根据《巴黎公约》的规定,“在工商领域任何与诚实商业惯例相悖的竞争行为均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正当竞争与不正当竞争仅有一线之隔,超出了这条线,正当竞争将演变成不正当竞争。这代表着,商标权作为控制行为的权利存在对行为控制适度性的问题。换言之,这是对商标权正当行使的要求,而商标权行使的正当性与否必须从竞争政策出发进行考察,考察其是否有利于促进和维护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从这一角度,商标权的限制是商标法不可或缺的部分。对此,我国在立法上与理论上应加深对商标法竞争政策内涵的认识,确立商标权保护应服务于促进竞争这一根本目标,不仅在商标权保护上与国际接轨,在商标权限制上也应当尽快实现这一接轨,否则,当权利的保护与限制不相适应时,商标法将产生更多反竞争因素。
商标权刑法保护的历史演进
无疑,迈进现代法治的我国要求法规范体系满足现代社会的不断扩张的要求。在商标权的刑法保护这一问题上,清末以降我国法规范体系的确立、发展以及完善是1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且其中夹杂着利益纷争与外国列强对旧中国的压榨欺迫。以史为鉴,能够明晰商标权刑法保护之不足与误区,由此为其完善提供1个有益视角。“它应当不仅是过去的历史的叙述,并且是未来的哲学的营养。”通过商标权刑法保护的百年回顾,结合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能够窥探出刑法解释学难以满足商标权刑法保护之需求,必须从刑法立法学上完善商标权刑法保护体系。
(一)从清末修法到民国“六法全书”
“在那个强权就是公理的海盗时代,中国的忍让并未换来西方国家的同情……变本加厉地压迫中国。”当西方列强叩开旧中国的市场大门之后,囿于彼时的清政府的法制状况,其对于诸如商标权保护等“法外治权”的渴求愈加强烈,一系列为了专门保护外国人的商标权的法律陆续出现在旧中国人的土地上。自1902年起,清政府相继与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签订涉及商标管理的条约,旨在防止假冒、保护商标。1904年,清政府在商务部内设立商标登录局,专门管理商标保护事宜。彼时的“保护商标”宗旨更多的是为美国等国服务,由于彼时的清政府企业尚不具备“走出去”的能力,并且国内市场对于现代商标权的保护体系需求并不强烈,完全能够以标示牌号等方式区别商家的商品或服务。1904年8月,清政府在被裹挟下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商标法律,即由其商务部制定而由光绪帝钦定颁布的《
注册商标试办章程》,该法规定了一系列侵犯商标权及犯罪的行为方式,例如在同种商品上使用与别人申请注册商标相似或相同商标的行为,或者贩卖上述假冒商标,或者明知上述情形而予以贩卖上述商品,等等。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部法律的代拟人竟是当时掌管旧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尽管其宗旨是保护美国等国的商标,在客观上也推进了现代商标法体系在旧中国的确立与完善。即使如此,也无法磨灭彼时中国人的法律制定权被外国人操控这一耻辱的历史事实。北洋政府1923年《商标法》是民国阶段的首部《商标法》,其将商标管理规范、商标权作为商标犯罪的保护法益,对于商标犯罪行为的规定较为全面,例如规定了欺诈获取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属于犯罪行为。1925年《商标条例》完全照搬了上述北洋政府的商标法律的规定,其规定了诸多侵犯商标权以及商标管理规范的犯罪行为以及刑事惩罚。并且1930年《商标法》以1923年《商标法》作为蓝本,但这部法律并未规定侵犯商标权以及商标管理规范的行为的刑事责任。同时,北洋政府1923年《商标法》规定,能够以刑法处罚侵害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而国民政府1930年《商标法》删除了这个规定。依据颁布于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以及第二百五十四条规定可知,对于构成犯罪的侵犯商标权行为,以妨害农工商罪进行惩罚。同时,该法规定的商标犯罪行为包含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伪造、仿造商标行为以及第二百五十四条规定的贩卖、陈列、输入、伪造、仿造商标、商号、货物行为。我国台湾地区于1972年修订“商标法”时,将商标管理规范作为保护法益,并以刑法处罚侵犯其之行为。除此之外,其对于商标犯罪的规制采取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结合型立法模式。总体而言,纳入商标犯罪的侵犯商标权行为相当广泛,包含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与商标相关)、伪造、仿造商标、商号行为。其规定的“假冒行为”意为,在类似或相同商品或服务上,使用近似或相同之申请注册商标或团体商标,有致相关消费者混淆误认之虞者,其外延很宽泛。其商标犯罪的侵害对象包含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团体商标、原产地商标以及未经申请注册的外国著名商标等。但其并未规定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申请注册商标标识罪,至于其构成其他商标犯罪的共犯情形,则是另1个问题。
(二)1979刑法典对商标权的保护介析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商标法规是由政务院制定并颁布的1950年《注册商标暂行条例》以及《实施细则》,工商业企业(经申请注册的)商标的专用权由其进行专门保护。当下的商标法律体系在相当程度上继受了这个条例的具体规定。从1957年至1979年止,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与思想观念闭塞等原因的存在,我国商标管理规范呈现出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从商标强制申请注册制度(未申请注册无保护)以及商标与商品质量挂钩制度中可见一斑。彼时,并未对侵犯商标权的行为规定刑事责任。直至1979年《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才规定了假冒申请注册商标罪。从这一立法规定可见,彼时的规范保护尚显粗糙。这个罪名的犯罪对象仅仅包含企业申请注册商标,犯罪主体仅仅包含工商企业,二者的范围皆较为狭隘,无法满足市场经济对于商标权的刑事法保护的要求。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的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注重对商标的保护和经营,同时,谋求在中国进行投资开发项目建设以及获取投资建设红利的外国企业,也更加注重其商标专用权在中国受到有效保护的强度。彼时的《商标管理条例》在相当程度上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必须,为了强化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力度,适应市场经济之要求,1982年《商标法》顺应时代的呼唤与商标保护的必须适时而出。这部法律的首要指导思想仍是商标工具主义,而不是商标权保护主义。由于其指出,应当强化对于申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力度,并且指出,商标使用人应对其商品质量负责。可见,申请注册商标专用权是国家用以规制商标权人负责商品质量的便利工具。诚然,申请注册商标专用权受到了商标法的保护,但这似乎仅仅是一种工具主义导向下的附随功能。随着我国的相关知识产权法律的逐步建立,加之认可商标权民事权利性的《民法通则》的正式实施,我国逐步加入了诸多重要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组织,商标之商誉受到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企业已经将注册商标作为一种保护企业的重要手段。基于我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的要求,同时为满足商标的国际申请注册与保护请求的相互往来需求,我国自1988年11月1日起,采纳了国际通行的《注册商标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以下简称为《尼斯协定》)。1979年《刑法》对于商标犯罪的简陋规定,无法适应彼时的实践中出现的打击严重侵犯商标权行为的必须,例如严重的(以出卖为目的的)擅自制造别人申请注册商标标识的重侵犯商标权行为,无法被科以刑事惩罚,这使得此类行为继续猖獗不止。我国通过逐步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并实施相关司法解释,扩大侵犯商标权的刑事法规制范围,并扩大商标犯罪的犯罪主体的适格范围,逐渐缓和了这一分歧。针对1979年《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1982年《商标法》第四十条扩大了假冒别人申请注册商标的行为方式类型,包含了擅自制造或者销售别人申请注册商标标的行为。随后,相关司法解释将“有意销售假冒申请注册商标的商品”之行为,作为假冒商标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并且将个人作为假冒商标罪的犯罪主体。为了有效地打击商标犯罪,营造更加
健康的市场经济竞争秩序,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国于1993年2月22日重新修订了《商标法》,其第四十条被修订为包含三款的法条,初步奠定了3个传统商标犯罪的商标法基础。随后,《关于惩治假冒申请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为《补充规定》),大部分是将以往对于商标权的刑事法扩大保护的内容囊括于中。总体而言,经过《补充规定》的修改,我国商标权的刑事法保护体系主要呈现四点转变:其一,在保留假冒申请注册商标罪的基础上,增加销售假冒申请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申请注册商标标识罪;其二,将犯罪主体从1979年《刑法》规定的工商企业(直接责任人员也作为责任主体),扩大到一般主体(包含企事业单位);其三,具化假冒申请注册商标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以及要素;第四,将商标犯罪的法定刑(量刑幅度)从一档增加至两档,突出罚金刑的功能。
(三)1997刑法典对商标权的保护介析
为符合TRIPs协议对于商标权的刑事法保护的总体要求,1997年《刑法》设置了假冒申请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申请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申请注册商标标识罪这3个侵犯商标权的罪名。这实质上是以基本法的形式吸收了1993年《补充规定》的商标权刑事法保护的罪名设置。1997年《刑法》在修订过程中,将商标犯罪、假冒专利罪、侵犯商业秘密罪、侵犯著作权罪等犯罪规定在侵犯知识产权罪一节中,由此组成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除此之外,1997年《刑法》修改了《补充规定》中的商标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为了更为合理地界定这3个商标犯罪的“罪量”标准,加强商标权刑事法保护的力度,《2004解释》对“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等“罪量”问题进行了专门解释,并且将“相同的商标”扩大解释为完全相同或较之视觉基本无差异且足以误导公众的商标,不仅将使用于商品上界定为“使用”,并且将使用于商品
包装、容器等其他商业范围上亦界定为“使用”。随后,《2011解释》对“同一种商品”的比较判定对象与“与其申请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判定方法等问题皆作出了明确规定,同时明确了值得刑法处罚的相关犯罪的未遂情形。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