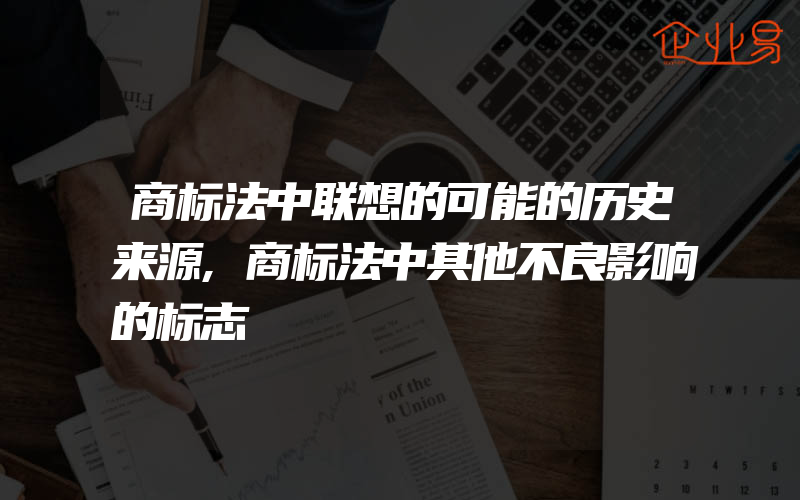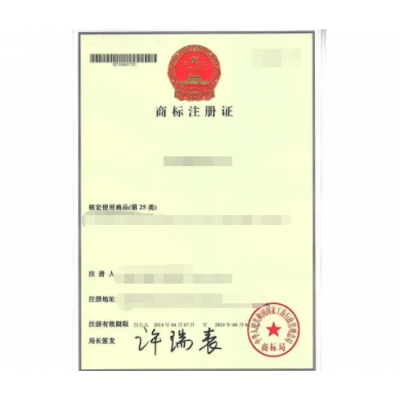商标法中联想的可能的历史来源
从1964年开始设立工作小组起草欧共体商标法算起,欧共体《指令》的出台经历了20多年的历程。其间不乏多次修改建议稿。在最初的条文中,并没有“联想的可能”的表述。不过,最终在1988年成文之时,“联想的可能”却被载入《指令》文本。很大程度上,这被认为是比荷卢三国尤其是荷兰代表团在立法中的坚持以及比荷卢三国统一商标法以及判例影响所致。比荷卢三国的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几乎就是现代欧共体的缩微版和实验版。包含比荷卢统一商标法的制定以及统一的比荷卢法庭的建立都为欧共体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由于当时的比荷卢三国集中了包含飞利浦在内的上千知名品牌,其商标保护实践相对丰富,因而在当时的欧洲大陆,比荷卢三国的商标法(包含司法判例)被视为是最现代的。当时的比荷卢统一商标法对欧共体商标《指令》产生影响也不足为奇。不过,比荷卢三国统一商标法经历过多次修订,该法首次于1971年1月1日在三国正式生效,取代原来三国各自的商标法规。1983年11月10日统一商标法被修改,1987年1月1日生效;为了适应欧共体协调法令,比荷卢联盟于1992年再次修改了商标法并于1996年1月1日生效。从时间进程上看,1971年生效或者1983年出台的三国联盟商标法及相关司法判例对欧共体《指令》产生的影响最大。而后,欧共体《指令》反过来又推动了1992年出台、1996年生效的现行三国联盟商标法。在1971年的三国统一商标法里,并没有“联想的可能”的踪迹。1971年的比荷卢联盟商标法里与侵权判定最相关的第13条的规定,尤其是第13条(A)(1)法条的措词,和中国现行商标法第52条第一项几乎没有差别。其间没有“联想的可能”,也没有“混淆的可能”的表述,是其独特之处。相关的文献表明,1983年出台的三国统一商标法也没有“联想的可能”的规定。“联想的可能”的最初来源,多被认为是比荷卢法庭判例法,即1983年的Union/UnionSoleure案。其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比荷卢三国商标法的框架下,在没有“混淆的可能”这一概念的情况时,法庭怎样判断商标近似?这恰好也是商标淡化判定中同样必须面临的问题。“当考虑到个案的诸如商标的显著性的特殊情形,在整体观察与对比观察之下,假如标志与商标听起来或者看起来或者观念上达到这样一种相似性,以至于标志与商标间的‘联想’被激发,则标志与商标就是近似的。”而到了1992年修订,1996年出台的比荷卢商标法第13条(A)(1)(b)里,则明白无误地将“在商贸活动中将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使用在与申请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上,使公众在使用标志与申请注册商标之间存在着‘联想的可能’的行为定性为侵权”。尽管1996年版的比荷卢商标法是为适应《指令》而修订,可是第13条(A)(1)(b)的规定不能当然地理解为体现了《指令》的精神,其表明的仅仅是比荷卢三国对于《指令》的理解。比荷卢三国对于《指令》的这种理解能够一直追溯到《指令》的立法进程。事实上,在指令出台的整个过程中,就侵权判定采用“混淆的可能”还是“联想的可能”的问题,比荷卢三国的立场与欧共体其他国家的立场分歧严重,比荷卢三国偏向于“联想的可能”,即当相同或者类似的商标使用在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上时,并不必须在相关公众中产生混淆,而只要产生了联想,商标权人就有权禁止。这显然比“混淆的可能”的判断标准要宽泛。在欧共体其他国家看来,这种过度的保护显然与自由贸易的目标背离,因此极力反对。最终形成的《指令》第4条、第5条代表了这两种观点的折中,但其措词令人困惑。由于一般而言,仅有大的概念包含小的概念。假如认为“联想的可能”比“混淆的可能”更为宽广,那么怎样理解“混淆的可能”能够包含“联想的可能”?比荷卢三国认为,这一表述宣布了“联想的可能”的判断标准的胜利。或许是由于这一原因,1996年的比荷卢三国商标法里的措辞直接使用了“联想的可能”的表述,而没有提及“混淆的可能”。然而,这种胜利宣言为时过早,立法上措词的妥协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由于《指令》的条文解释最终取决于欧共体法庭(ECJ)。不幸的是,直到比荷卢三国商标法生效之后的1997年,ECJ才有机会在Pumav.Sabel(C‐251/95)案中对于“联想的可能”的理解做出正面回应。使比荷卢三国沮丧的是,AGJacobs在其意见书中断然否认《指令》立法进程中的谈判备忘录能够作为解释《指令》的依据。随后一系列的欧共体法庭案例表明,比荷卢三国认为在《指令》中“联想的可能”取代“混淆的可能”的理解遭到完全的否决。在此之后,比荷卢三国商标法中“联想的可能”的条款13(A)(1)(b),在2004年的比荷卢三国知识产权法(商标与外观设计)修订的过程中,也被完全取缔。其修正后的相关条款的表述,与欧共体《指令》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商标法中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
《商标法》第十条第1款(八)后半句规定,“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从文义来看,“其他不良影响”应是不同于道德风尚的影响。然而实务中,商标评审委员会和法院时常把道德风尚的负面影响认作“其他不良影响”。前文“资本家CAPITALIST”、“DANDY”和“乡巴佬”的裁判意见,便是如此。严格讲,这种便宜行事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其他不良影响”按理应理解成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负面影响,而不应具有道德风尚的内涵。《商标审查指南》2005指出,“其他不良影响”是指“商标的文字、图形或者其他构成要素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的、负面的影响”。(以下情况也属于不良政治影响:标志有损国家主权、尊严和形象(例如,不包含台湾地区的中国地图,有损祖国统一;标志使用“福尔摩沙”,此为殖民主义者对我国台湾地区的称谓);标志含有具有政治意义的数字等构成(例如,918,911);标志整体或部分与恐怖主义组织、邪教组织、黑社会名称或者其领导人物姓名相同或近似(例如,“拉登”);标志带有种族歧视性(例如:“黑鬼”;“Honky”白鬼子)标志作为商标使用,假如有害于宗教信仰、宗教感情或者民间信仰,也属于“其他不良影响”。宗教包含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以及它们不同教派分支。民间信仰主要包含妈祖等民间信仰。在“其他不良影响”条款下,以下宗教信仰相关标志适用类似于国家名称等特殊标志的法律保护:宗教或者民间信仰的偶像名称、图形或者其组合(例如,观音;妈祖等);宗教活动地点、场所的名称、图形或者其组合(例如麦加、雍和宫等);宗教的教派、经书、用语,仪式、习俗以及宗教人士的称谓、形象除此之外,根据《商标审查标准》,“其他不良影响”条款对以下标志也予以特殊保护:我国各党派、政府机构、社会团体等单位或者组织的名称、标志;我国党政机关的职务或者军队的行政职务和职衔;各国法定货币的图案,名称。)对特定私人利益产生的不良影响,则不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1款(八)所谓的“其他不良影响”。《审理商标授权确权纠纷的司法意见》明确指出,“假如有关标志的申请注册仅损害特定民事权益,由于商标法已经另行规定了救济方式和相应程序,不宜认定其属于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对何谓“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也举数例说明。假如标志整体或部分地同政治人物姓名相同或近似,可因具有不良影响而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和申请注册。例如,“毛大爷maodaye”(指定商品项目34类香烟、雪茄烟、烟丝、嚼烟等),依据字面意思是指姓“毛”的长者。然而,在没有上下文或其他因素可明确另有指代对象时,社会公众自然会联想到已故国家主席毛泽东。为此,法院认定文字商标“毛大爷maodaye”具有“其他不良影响”。又如,将政治、宗教、历史等公众人物的姓名作为商标注册申请申请注册,足以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的,能够认定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例如,鲁迅长孙周令飞曾试图将“鲁迅”申请申请注册用于第33类黄酒、米酒等商品。商标局驳回申请,认为鲁迅是我国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作为商标使用具有不良影响。另,某人以“冰心”申请注册商标用于第3类白酒、米酒、葡萄酒等商品。法院认为,“冰心”是我国著名作家谢婉莹的笔名,她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享有海内外的威望,为维护我国文化传统、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冰心先生,不宜核准申请注册为商标,“冰心”申请注册使用到白酒、黄酒之类的商品上,易产生“其他不良影响”。假如标志具有宗教含义,用于世俗社会可能会伤害相关信徒的宗教情感的,则可认定“具有其他不良影响”。例如,1997年8月22日,上海城隍珠宝总汇向商标局申请申请注册“城隍”商标。作为国有企业,上海城隍珠宝总汇于1997年10月24日被批准整建制地归并给上海城隍庙第一购物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并于同年注销。2009年6月8日,上海城隍庙第一购物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为上海城隍珠宝有限责任公司,而“城隍”商标于2010年核准申请注册,核定商品项目为第14类“宝石、金刚石、珍珠(珠宝)”等。该公司旗下的“城隍”珠宝品牌,曾先后荣获“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商业名牌”“中国珠宝首饰业驰名品牌”等多项荣誉。中国道教协会认为“城隍”申请注册商标违反《商标法》2001〕第十条第1款第(八)项,请求宣告其无效。所谓“城隍”,“城”原指挖土筑成的高墙,“隍”原指没有水的护城壕。我国古代传统民间信仰认为与他们的生活、生产安全密切相关的事物都有神在,于是“城”和“隍”被神化为城市的保护神。后来,道教把城隍纳入神系,作为剪除凶恶、保国护邦之神,“城隍神”逐渐成为古代汉民族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衹之一,主要由有功于地方民众的名臣和英雄充当,供奉于“城隍庙”中。“城隍”崇拜盛行于中国、越南、朝鲜半岛,也见于其他华人、越南人、朝鲜人聚居地。本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认为,尽管“城隍”具有“护城河”等含义,但“城隍”也被用于指代道教的特定神灵。在此情形下,将“城隍”作为商标加以使用,将对信奉道教的相关公众的宗教感情产生伤害,并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违反了《商标法》2001)第十条第1款第(八)项的规定。在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尽管应当考虑相关商业标志的市场知名度,尊重相关公众已在客观上将相关商业标志区别开来的市场实际,注重维护已经形成和稳定的市场秩序,但这种尊重不应违背商标法的禁止性规定。即使争议商标经使用具有较高知名度甚至曾被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也不应因此而损害法律规定的严肃性和明确性。另一方面,法院又承认标志本身含义带有不良影响,可由于持续使用而淡化,不再有“不良影响”。例如,“酒鬼JIUGUI及图”申请注册商标,自1988年即在酒类商品上使用,经使用获得国内国际多项荣誉,2000年被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法院认为,“酒鬼”虽有“酗酒且经常喝酒的人”等含义,但争议商标使用多年并获得系列荣誉,无证据表明在消费者中产生了不良影响,不违反《商标法》2001)第十条第1款(八)。本案裁判意见不代表着法院要求有证据表明在消费者中产生不良影响,方才适用“其他不良影响”的规定。否则,“毛大爷”案、“冰心”案的判决意见将无法解释。这只表明法院偏向于维护多年使用而具有良好声誉的商标。除此之外,为遏制不当的商标注册申请行为,商标评审委员会和法院近些年创新地把“其他不良影响”解释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例如,纪某在2002-2003年两年内相继申请申请注册160多件商标,包含:“彪马PUMA及图”、“圣罗兰YVESSAINTLAURENT及图”;“花花公子PARTYBOY”;“梦特娇MONTAGUT及图”;“金利来GOLDLION及图”;“劳斯莱斯ROUSIREISI“SK-2”;“雅芳AVON";“法拉利FERRARI”;“路透社REUTERS”等。法院认为,纪某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大批量申请申请注册与别人有一定知名度商标相同或类似的商标,但无实际使用意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会导致对我国经济、文化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故具有“其他不良影响”。当然,这种做法更多是权宜之计。本案中,倘若纪某只申请有上述商标之一的话,法院若评价其行为为“其他不良影响”则显得有些牵强。然而,纪某行为的法律性质并不取决于数量,而决定于其行为的本质特征。纪某行为的可责性不在于申请多件与别人有一定知名度商标相同或类似的商标,而在于没有实际使用意图而申请申请注册商标。由于,我国商标法并没有要求申请人必须具有实际使用商标的意图,因此,这也可看作法院企图以“其他不良影响”来弥补这一制度的缺憾。当然,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际上,以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由而适用“其他不良影响”条款,已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是法律适用错误。对上述商标抢注行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又曾判定为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商标”,违反《商标法》2001]第四十一条第1款(同《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1款)。同时,为遏制自然人无使用意图的申请申请注册商标行为,商标局2007年出台部门规章,规定“自然人提出注册商标申请的商品和服务范围,应以其在工商营业执照或有关登记文件核准的经营范围为限,或者以其自营的农副产品为限”。《商标法》第七条还笼统地规定“申请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但却未规定违反的法律后果。如此种种解决方案,真可谓“九龙治水”。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商标法未来修订应该将真实使用意图列为商标核准申请注册的前提条件,对违者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商标”论处。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