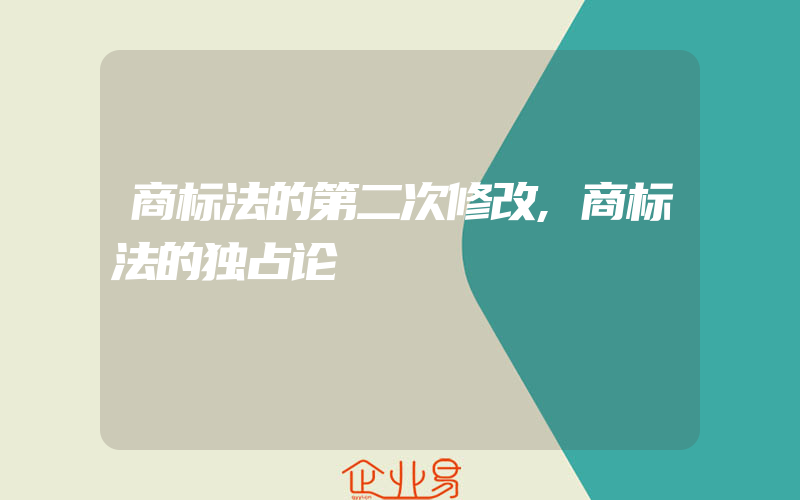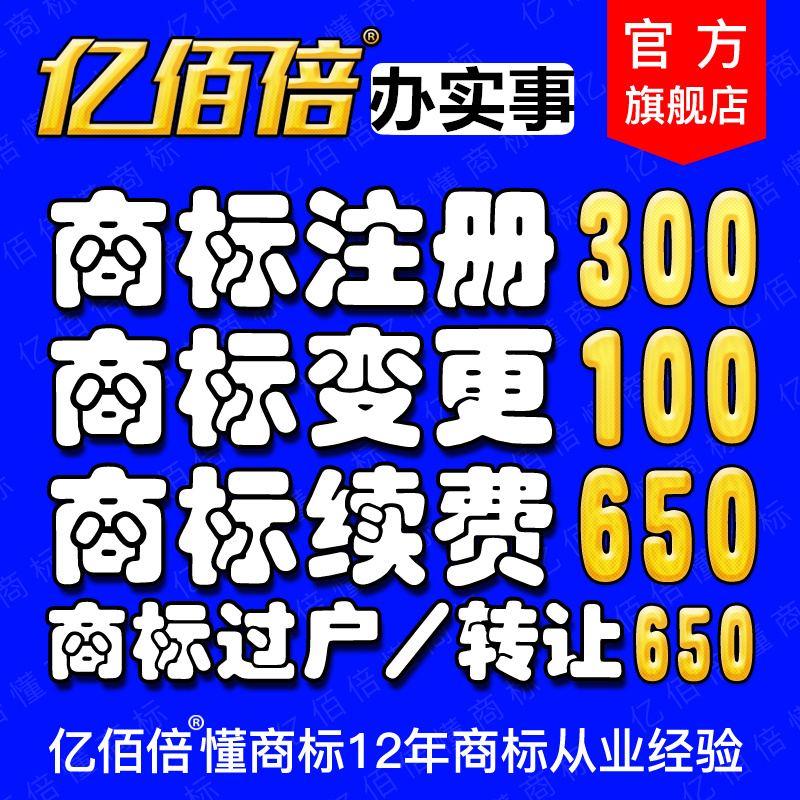商标法的第二次修改
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商标法的决定》,从进1步完善我国商标法律制度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履行我国入世谈判承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出发,对1993年《商标法》与国际条约和TRIPS协议存在差距的条款和其他不完善的条款作了修改。这次人大常委会尽管是采用修改决定的方式对《商标法》进行修改,但从修改的内容看,则接近于对《商标法》的一次全面修订。1993年《商标法》43条,经过这次修改,增加到64条,其中,删并了2条,改动了22条,增加了23条,未作修改的仅有19条,也就是说,在新《商标法》中,①新增加或修改的内容占全部内容的三分之二以上。《商标法》修改的内容涉及到许多方面,可是,归纳起来讲,突出在两大理论贡献上。首先,商标权的私权性质得以显现。这能够从如下方面体会:(1)修改后的《商标法》1个主要特点是在商标权的获得与维持方面引入了司法审查制度,更加尊重商标权人的权利,而不再把商标权作为一种单纯的行政控制的对象,对商标所有人的权利从获得到维持更加注重实然状态向应然状态的转化。(2)注册商标人有权标明“申请注册商标”或者申请注册标记,这与原《商标法》第7条规定的使用申请注册商标应当标明“申请注册商标”或者申请注册标记显然存在差异。在前者,商标权是一种能够自由处分的权利,商标权人能够在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上标明“申请注册标记也能够不这样做;而后者,则是着重强制性规范,是对义务的规定,商标权人没有选择权,只能遵守,这种情形下的商标权更多了公权的性质。(3)对因侵犯商标权而引起纠纷的解决途径,当事人能够选择,排除公权介入,实行“不告不理”或“告诉才处理”原则,并且即使在行政机关介入的情况下,当事人仍具有申请调解权。(4)增加了自然人作为商标权主体和两个以上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共有商标权的规定②应该说商标法通过(3)、(4)两条的规定从主体的角度更多地赋予了商标权的私权性质。其次,代表了先进的民法理论。国内有学者称赞2001年修改的《商标法》代表了“民事立法的方向”。③的确,新《商标法》在中国民法理论上的贡献至少有以下几点:(1)在商标的区别功能得到毫无疑问的基础上扩展了商标的信誉功能。1983年开始实施的商标法的最主要功绩在于,恢复承认商标的区别功能,承认并规定申请注册商标人的商标专用权。而201年修改的《商标法》将商标提升到了更加先进的权利地位,从保障消费者、生产者和经营者利益的角度强化了维护商标信誉的重要性。商标信誉的突出,使得商标权的民事权利地位向高级纵深方向寻求法律支持。(2)突出对“在先权”的保护,确立了商标“在先性”的本质要求。与商标的私权性质相一致,不仅申请注册在先能够取得商标权,并且在先使用商标和“驰名”在先的商标也是商标权产生的先决条件,使商标成为市场经济的产物。(3)从全面保护“权利物权”的高度认定了商标权作为绝对权(对世权)的重要性,即对商标权权利主体以外的义务主体而言禁止假冒和禁止反向假冒,从而使“商标专用权”的概念更加接近于“商标权”,它预示着商标专用权不仅仅是债权的“专用权”,还是“权利物权”意义上的“专有权”。(4)无过错不负“赔偿责任”,以及“即发”而未发的侵权仍旧要负侵权责任的规定,更改了民法学界多年来有关认定侵权需有“四要件”的通说,亦即否定了“无过错不负侵权责任”,“对权利人造成实际上损害方能认定侵权”等长期以来形成的“侵权法”定论,这转变将对民法产生重大影响。
商标法的独占论
“独占论”完全无视知识产权的公共政策内涵,将知识产权作为权利人跑马圈地、攫取财产的手段,将知识产权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公共利益之上。这种思潮如引入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将使知识产权制度整体背离激励竞争的制度价值而沦为一部纯粹的财产法。“工具论”清楚地认识到了知识产权对于实现公共政策的工具性意义,主张对知识产权的有限保护,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应服务于公共政策。落实到商标法领域小编认为,“工具论”正确揭示了商标法律制度的要义在于维护和促进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商标权的保护应服务于这一价值而不应有所逾越。“醉翁之意不在酒”,通过商标法保护商标权的用意不在于保护商标权本身,而在于国家竟争政策的执行。因此,应充分认识到商标权保护的工具性意义所在,保护商标权制度的价值理性在于维护和促进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假如将保护商标权的工具理性代替了商标法的价值理性,其结果将本末倒置,迷失了商标法律制度的本义,是对商标法的误读。因此,解决商标法悖论的关键在于对商标权保护进行合理定位,对商标权的财产地位进行合理定位。尽管以“混淆理论”为基础的商标权保护和以“财产理论”为基础的商标权保护都创立了商标“财产”制度,但在财产的内涵和受到保护的程度上却大不相同。仅有从维护和促进公平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理解商标权的财产属性,设计商标制度,进行商标司法和行政执法,才可能实现商标法的制度价值。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的任务是调和各种相互冲突的价值目标,在多元价值格局中找寻最佳平衡点。商标法是1个融多元价值于一体的法律体系,其中保护商标权是商标法的基础价值,保护消费者是商标法的延伸价值,促进和维护公平有效市场竞争是商标法的核心价值。在商标法的诸价值中,如上所述,商标法的基础价值——保护商标权,与商标法的延伸价值——保护消费者利益原则上是一致的。而对于商标法保护商标权这基础价值与促进和维护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这一核心价值之间的关系,我们却应当一分为二地来看待。当对商标权的私权保护与保护消费者、其他竞争者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公共利益达到一种合理平衡时,对商标权的私权保护将有效地实现其促进和维护公平有效竞争这一政策目标,当对商标权的私权保护无视消费者利益、其他竞争者利益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公共利益时,商标权的私权保护将成为促进和维护公平有效竞争的阻碍。因此,在商标立法以及商标权的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中,应当深刻理解商标法的价值结构及各价值之间的关系,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契合,实现商标权人与消费者、其他竞争者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使对商标权给予保护的同时彰显商业伦理、激励正当的商业竞争。尽管知识产权具有财产属性,但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仍然存在适度性的问题。包含商标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的非理性扩张必然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使知识产权法的实施出现反竞争效果;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到位,没有起到足够的激励作用,同样也将使知识产权的实施出现反竞争效果。美国在20世纪初期和20世纪80年代所采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专利政策对这一问题有一定的说明力。20世纪初期,美国在一段时间曾经采取对专利权进行严格控制的制度。这种严格控制主要表现为:一是严格授予专利权的标准,二是加强对专利权的反垄断控制。这专利制度大大挫伤了技术发明人研发和申请专利的主动性,也给了国外侵权者以可乘之机。(1经历了七八十年代的经贸危机后,美国在反思中调整了过紧的专利制度,转而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这种宽松的专利管理政策,使发明人的权利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专利申请和授权量迅速攀升,但这种过于偏向于专利权人的管理规范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如专利申请过多、过滥导致专利质量良莠不齐以及专利丛林现象,扰乱了正常的竞争秩序。商标权保护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过度保护或保护不力都会产生抑制竞争的效果。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