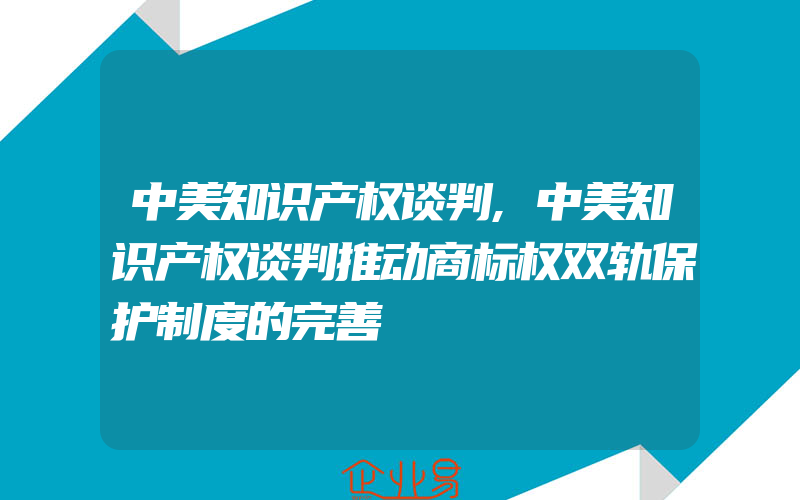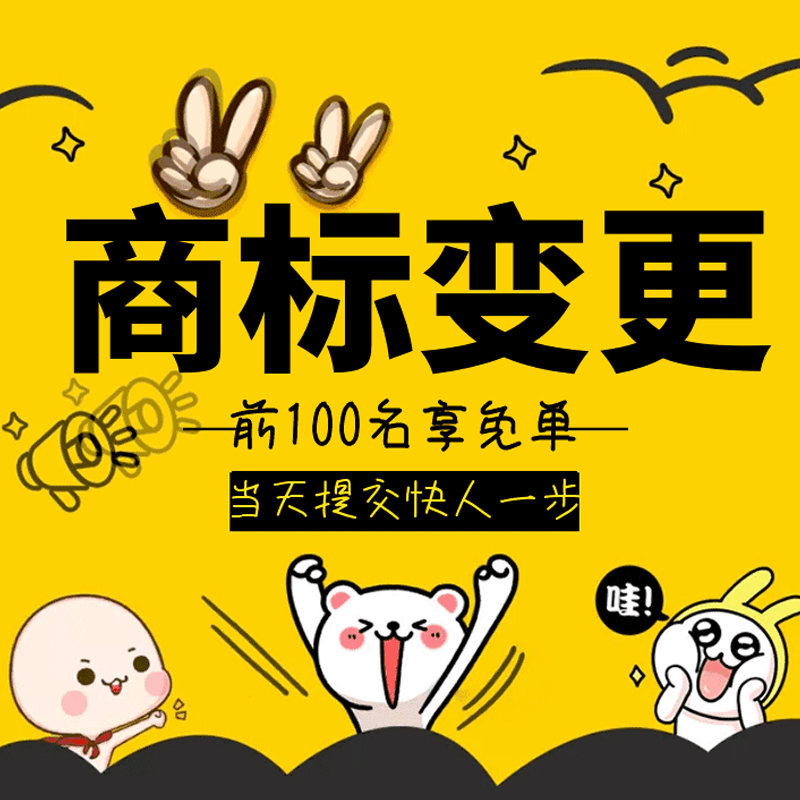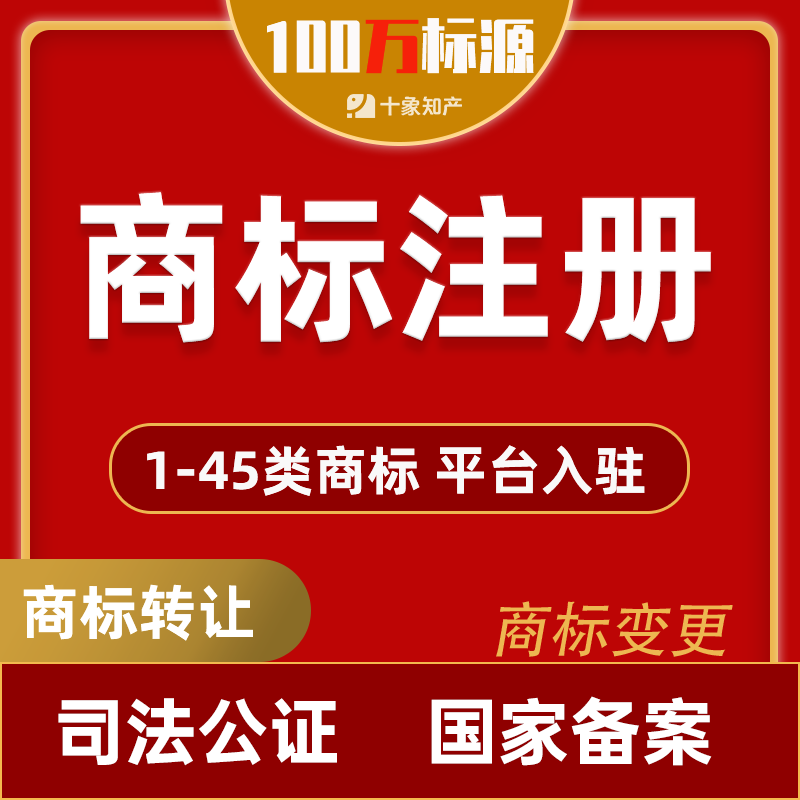中美知识产权谈判
自1989年开始,中美双方在1989年、1991年、1994年、1996年、2004年、2005年进行过多次知识产权问题谈判,其中几次磋商都濒临破裂、引发贸易战的边缘。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次。即:1991年4月底,美国对中国发起“特殊301调查”。同年12月3日,美国宣布进行贸易报复,同一天,中国宣布进行反报复。1994年6月底,美国再度启动“特殊301调查”,同年12月31日,美国宣布进行贸易报复,同一天,中国宣布进行反报复。1996年4月底,美国又启动“特殊301调查”,半个月后的5月15日,美国宣布进行贸易报复,同一天,中国宣布进行反报复。在中国加入WTO以后,美国又开始借助于WTO的有关程序来解决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问题。2007年4月10日,贸易代表办公室向WTO终端解决机制提起磋商请求,发起针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和出版物市场准入问题的诉讼。长期以来,中美双方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分歧始终十分尖锐。应该说,中美双方在知识产权问题的一轮轮较量与中美总体贸易形势和现状、美中贸易逆差巨大和每一任贸易代表的态度,都有着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在上述这些知识产权交锋中,第一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焦点,对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司法和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第一次(1991—1992年)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突起1991年4月26日,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大使向新闻界宣布,根据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竞争法》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特殊301条款”而进行的年度审议结果,决定将中国、泰国、印度三国列为未能对美国的知识产权提供充分、有效保护的“重点国家名单”。按照美国的法律,此决定宣布1个月之后,贸易代表办公室有权对该国的行为和政策发起调查。5月9日,中国经贸部发言人指出,美国的做法是不公正的也是中国方面不能接受的。然而5月26日,调查程序还是开始了。中美两国政府经多次协商,中国驳回了美国的无理指责和漫天要价,1992年1月17日终于在华盛顿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签字的中国政府代表是当时的外经贸部副部长吴仪,美国政府代表是贸易办公室主任卡拉?希尔斯。2.六个争论焦点此次中美两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争论的焦点主要有六个:第一,关于我国专利法中强制许可的规定。1984年的中国专利法规定,专利权人有在中国自己实施或容许别人实施其专利的义务,假如3年内没有正当理由未履行义务,专利局有权给予实施该专利的强制许可,而不论发明人是否愿意,但实施人必须给专利权人付以合理的使用费。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发明,尤其在自然灾害、战争等情况下,强制许可的权利十分重要。这项规定对于申请了中国专利的外国人同样适用。美国人则认为,1个拥有中国专利的美国人,能够在美国制造专利产品其次卖到中国,也应该被认为是实施了该专利。这与我国专利法的规定大相径庭。由此美国政府认为我国保护美国人的知识产权不充分。第二,关于化学制品和药品的专利保护。我国1984年颁布的专利法规定,对药品和用化学方法获得的物质不授予专利权。美国人一直对此耿耿于怀。由于美国每一年用于新药的研制和开发费用约100亿美元,而每一种新药从挑选新化合物到批准投入生产平均支出约2亿美元、10~12年时间,此后,若有人运用逆向工程,只需花十几个月、数百万元即可达到相同的目的。于是美国人多方出击,要求发展中国家给予药品以专利保护。在中国当时专利法不保护药品和化学物质的情况下,美方提出对于那些美国新研制出的、在美获得专利的新药和化学物质,要用行政手段保护其在中国的市场。第三,关于著作权法的修改。从1991年6月1日起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对于那些从事绘画、影视、音乐的艺术家们,那些职业非职业的作家、记者及千千万万个热衷于爬格子的中国人而言,当他们的作品一出世,就自然得到了著作权。可是,由于我国还不是《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的成员国,故对于外国人首次在国外发表的作品,我国当时的著作权法不予自动保护。事实上,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经历了这个过程。《伯尔尼公约》诞生于1886年,100年后,美国人方才加入,可见该公约的严格约束力了。美国人提出要求中国修改著作权法并限期加入《伯尔尼公约》,此时,中国的著作权法才刚刚生效20余天。第四,关于计算机软件的保护。我国在1991年5月24日颁布了版权法中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并于当年10月1日起施行。这个条例尽可能宽地保护了软件创造人员的智慧劳动,并且也像版权一样,自作品出世起自动享有版权,而不论是否已经商业应用。但却要求登记是取得诉权的前提条件,保护期限并非一般作品版权的50年,而是25年,但可续展25年。美国人则要求将计算机软件作为文字作品保护,也就是说不必履行任何登记申请注册手续,并应该像一般文学艺术作品一样,享有50年的保护期。第五,关于唱片保护。美方要求中国限期加入《保护唱片制作者防止其唱片被擅自复制的公约》(以下简称《日内瓦国际唱片公约》),并对已出版的但未过保护期的唱片也要给予保护。第六,关于商业秘密保护。当时,我国尚无明确法律规定保护商业秘密。3.谈判结果这次谈判使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达成了《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并对以上问题的解决达成协议。(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做了较大的修改。①专利权的享有不因发明的地点、技术领域以及产品进口或当地生产而受到歧视,政府的强制许可受到严格的限制;专利权被授予以后,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专利权人有权禁止别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进口依据其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②专利应授予所有的化学发明,包含药品和农业化学物质,而不论其是产品还是方法;③发明专利的保护期限为自专利申请提出之日起20年;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10年,不再续展。(2)专利法修改以前,我们承诺采取行政措施有条件地保护美国已有专利的药品、农业化学物质产品的发明。上述产品的发明人应向中国主管部门提出要求行政保护的申请,中国有关主管部门将向行政保护申请人发给授权制造、销售该产品的行政保护证书,并在行政保护期内禁止未获得行政保护证书的人制造或销售该产品。行政保护期为自获得该产品的行政保护证书之日起7年零6个月。行政保护自1993年1月1日起施行。(3)1992年7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通过我国加入《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的议案,该公约于1992年10月15日在中国生效。1992年7月30日我国政府递交《世界版权公约》加入书,1992年10月30日我国成为该公约成员国。(4)1993年1月4日,中国政府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了《日内瓦国际唱片公约》加入书,并于1993年4月30日起,中国成为该公约的成员国。(5)中国政府同意,不迟于《伯尔尼公约》在中国生效之日,承认并将计算机程序按照《伯尔尼公约》的文学作品予以保护。按照《伯尔尼公约》规定,对计算机程序的保护不要求履行手续,并提供50年的保护期。(6)1993年9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次会议通过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并于同年12月1日起施行,该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次谈判及随后的立法工作,使中国知识产权的立法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实际的司法保护水平不足,又引发了另一次知识产权大战。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推动商标权双轨保护制度的完善
1989年以后,随着中美外交关系的不断深入,双方的合作开始遍及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同时双方关系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单个方面,而是经济问题中混杂着法律及政治问题,政治问题中隐藏着经济利益纠纷。在知识产权方面更是如此,1个具体问题往往牵涉到双方在法律、经济及政治上的诸多利益,并且往往由中美双边关系影响到与其他贸易伙伴间的多边关系。而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日益加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尤其是对其跨国集团在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的保护成为美国发展对外关系中的一大重点。为应对此种局势,美国出台了《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法》。该部法律的出台使得美国政府有权采取单边手段对其认为损害其跨国集团及国内市场知识产权利益的他国行为进行调查和报复措施。此后中方就双方贸易纠纷中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斗争、谈判与妥协,从侧面进1步促进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随着美国对其本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升级,中美双方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分歧再次紧张起来。1989年5月,中美双方就贸易关系中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了重新谈判,中国被迫再一次提高本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以美国不把中国划为“特别301条款”为条件,中国承诺将计算机软件也予以版权,并延长专利保护期限。双方将达成的协议签署在一份备忘录草案中。遗憾的是,该备忘录还没来得及正式签署,美国便率先违反了先前许诺,将中国列入名单之中,中美知识产权关系发展的上升趋势也开始发生转折。1990年,中国再次被列入名单。不过,随着中国国内版权保护的呼声日起,我国仍于1990颁布了《著作权法》。其中第三条仍旧依据中美先前共识将计算机软件纳入到著作权保护中来。然而,就当时的形势而言,中国对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所作出的努力仍旧不能满足美国日益增长的知识产权保护需求。第2年,中国最终没有摆脱美国施压,由名单国家被划入到重点观察国家中来,这在中美贸易关系纠纷中尚属首次。同年美国据此发起了针对中国与美国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调查,指控中国没有提供充分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没有给美国公民提供其所要求的市场准入机会。并据此罗列出了四项具体指控,要求中方按美方要求做出改善。美方甚至借此发出了恐吓令,扬言或者中方改变或者受到美方报复措施。由此引发了中美建交以来双方就双边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冲突的首次对峙,并迅速转化为双方谈判局面。谈判的争议点集中在以中国改进包含专利权、著作权在内的六项知识产权制度问题上,而焦点则在于是采用美方的高标准1步到位还是按照中国模式缓缓前进。从根本上而言,双方的冲突主要是由于各自国内经济发展的水平差距,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也不同,中国认为保护宜宽松而美国则认为保护宜严紧,双方出于各自国内经济发展利益,均不肯妥协,双方谈判一筹莫展。同时对华最惠国待遇是否延长问题的引入又使本已陷入僵局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雪上加霜。最终通过中国政府的让步与美国布什政府在其国会的积极斡旋,美方终于同意取消对华实施“特别301条款”。双方于1992年通过了第1个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即中国与美国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根据备忘录要求,中国在1992年第一次对《专利法》进行了修改,将备忘录中所达成的内容加入进来。其中包含保护范围、期限、相关程序完善等问题。同时根据要求,中国也对《商标法》进行了相应修改,完善了商标的保护范围并加大了保护强度。上述修改,主要是基于1992年中美谈判所达成的备忘录而进行的,是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中国第一次就知识产权问题做出妥协以换取经济发展利益的举措。不过,就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上述修改也基本符合当时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崛起的需求。1992年中美谈判虽以双方最终达成共识而结束,但也只是暂时解决了双方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剑拔弩张的态势,备忘录的签署看似是风波的结束,实则是双方在知识产权领域展开的旷日持久的对峙的开始。在备忘录中中国的妥协主要限于制度构建方面,而没有在执法效果上给予美国承诺。显然美国不会始终满足于中国在和解后的执法状况,因而美国开始进1步就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实施提出更加明确的想法。特别是对备忘录签署后,中国知识产权执法状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加恶劣标明抗议。1994年,中国再次被美国列为重点国家。由此中美双方就双边贸易中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实施进行了第二次谈判磋商。美方代表对中国执法方式和执法队伍构建等问题提出了三项具体要求,而中国认为,美方的要求已超出了两国贸易谈判的经济利益范畴,怎样执法是中国内政,美国是霸权主义行为。由于谈判从贸易关系问题上升到了中国司法自主权这一敏感政治问题,使得双方分歧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愈演愈烈,并准备相互展开贸易报复措施。不过,中美关系随着双方交往的深入毕竟已与1979年中美建交时大不相同,中美贸易大幅上升,中美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为此后中美双方达成谈判共识提供了基础。双方都清楚,相互报复只会使双方都受到重大损失而没有实质益处。有鉴于此,中国政府首先向美方抛出了橄榄枝,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惩治知识产权侵权的执法活动,并主动表态会严格执行相关知识产权法律,用实际行动向美方表明了希望双方尽快达成和解的诚意。1995年,中美签署了双方的第2个知识产权保护协议。根据协议要求,中美谈判结束后,中国政府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均出台了一些关于知识产权执法问题的文件,并开展了大量的侵权执法工作,强化了海关管理,在社会上进行了大量的知识产权普及宣传工作。此后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不仅在法制化水平上有了较高提升,同时在执法的落实上也得到了明显改进。不过,中美双方的冲突似乎还未结束,这之后1年,双方贸易代表又先后举行了十八次会议,就美方认为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执法力度欠缺、海关没有进行有效的边境执法、美国厂家和产品没能依法准入中国市场等问题进行了大量博弈斗争。1996年,美国第三次将中国划为重点国家,并提出了比上两次更为过分的制裁计划,双方关系迅速转冷,并已做好相互报复准备。可是,1996年的中美关系,尤其是双方在经济利益上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密,双方在知识产权制度方面也建立了基本共识,谈判的立场已不再像前两次那样南辕北辙。就美方而言主要是为了解决逆差困境,而对我国而言,吸引外资,对外开放,是发展中国经济的总方针,中国也希望与美国达成共识。这使得双方谈判迅速达成了一致意见。同年6月中美签订了第3个知识产权协议,两国就侵权打击、执法深度、海关管理、市场优化等方面再次达成了一致意见。从内容上不难看出,该协议已与前两个协议侧重中国法制的完善不同,而更加侧重于行动和效果上的承诺。这个协议的签订,使中国避免了中美互相贸易制裁所带来的巨额经济损失,同时也为两国贸易关系的进1步发展提供了保证。之后,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关系一直围绕着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而酝酿、发酵并最终和解妥协,在美国的不断施压及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内驱力下,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和执法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从法律规定的完善,转而更加侧重要求法律的执行效果以及市场准入问题。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在商标权保护领域的立法与执法工作也因之作出回应,一方面依托商标行政主管机关,多次开展专项检查,完善执法措施,不断加大侵权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加强司法机关建设,增强法院系统在商标权保护中的作用。因此,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直接推动了中国商标权双轨保护制度的进1步完善。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