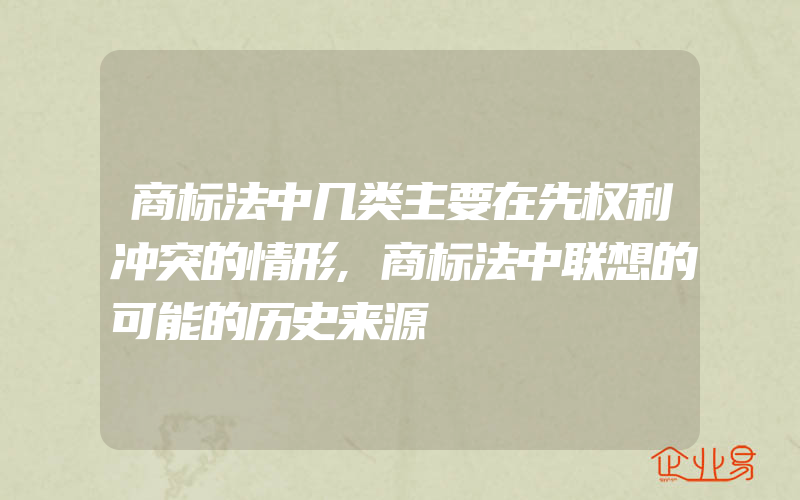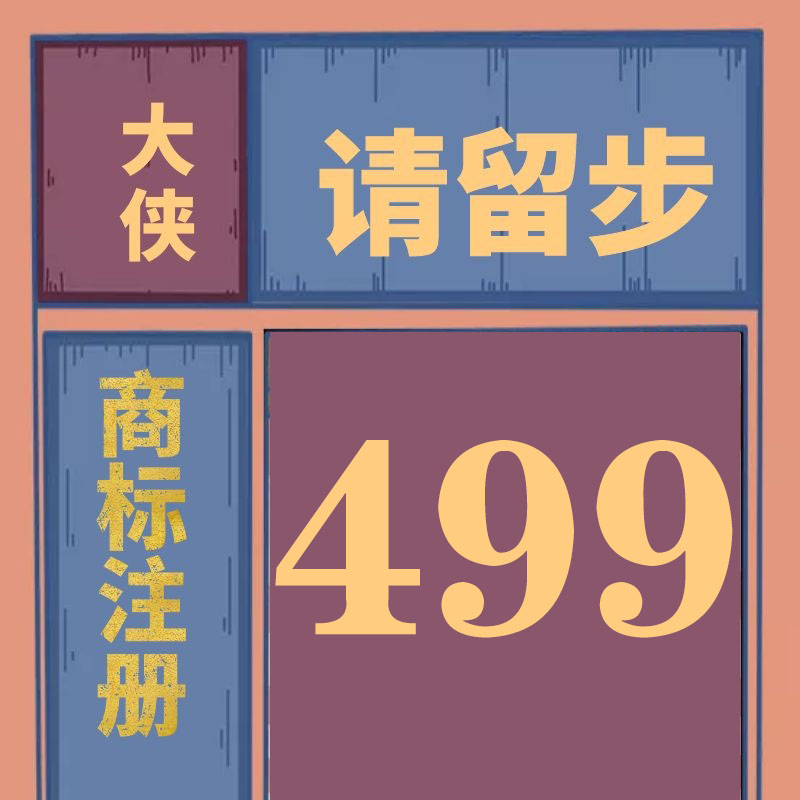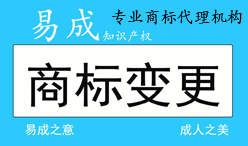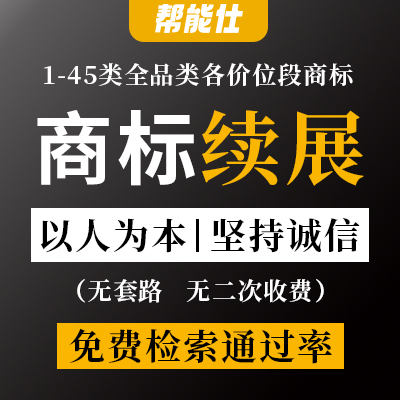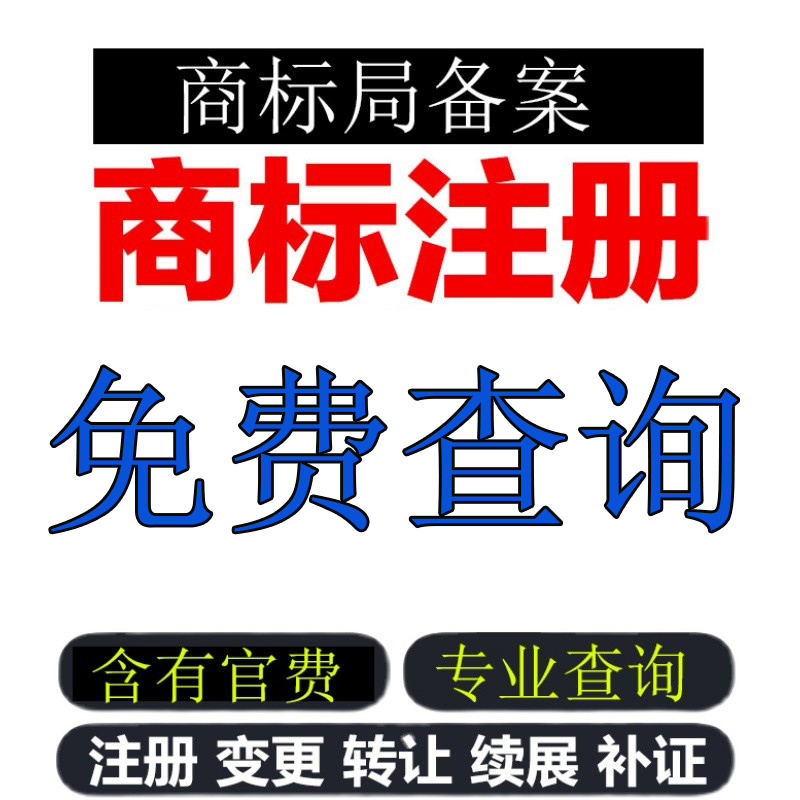商标法中几类主要在先权利冲突的情形
(一)在先著作权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将别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申请申请注册商标,应认定为对别人在先著作权的侵犯,系争商标应当不予核准申请注册或者被宣告无效。裴立、刘蔷与山东景阳冈酒厂的《武松打虎》案就是商标侵犯美术作品著作权的典型案例。被告景阳冈酒厂将原告裴立之亡夫、刘蔷之亡父创作的《武松打虎》组画中的第11幅修改后用于商标,侵犯了原告等享有的著作权。在符合下列要件时,商标与在先著作权冲突:1.系争商标与别人在先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在先享有著作权是指,在系争商标注册申请申请注册日以前,别人已经通过创作完成作品或者继承、转让等方式取得著作权。在先享有著作权的事实能够下列证据资料加以证明:著作权登记证书,在先公开发表该作品的证据资料,在先创作完成该作品的证据资料,在先通过继承、转让等方式取得著作权的证据资料等。对生效裁判文书中确认的当事人在先享有著作权的事实,在没有充分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能够予以认可。假如系争注册商标申请人能够证明系争商标是独立创作完成的,则不构成对别人在先著作权的侵犯。2.系争注册商标申请人接触过或者有可能接触到别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3.系争注册商标申请人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系争注册商标申请人应就其主张的取得著作权人许可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假如申请人能够证明系争注册商标申请人与著作权人签订了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或者著作权人作出过直接的、明确的许可其使用作品申请申请注册商标的意思标明,则该条件不成立。(二)在先外观设计专利权未经授权,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将别人享有专利权的外观设计申请申请注册商标的,应当认定为对别人在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侵犯,系争商标应当不予核准申请注册或者被宣告无效。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商标与在先外观设计专利权相冲突。1.外观设计专利的授权公告日早于系争商标注册申请申请注册日及使用日当事人主张在先享有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应当提交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年费缴纳凭据等证据资料加以证明。2.系争商标与外观设计使用于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系争商标与外观设计应当使用于相同或者类似商品。假如商品不相同或者不类似,则不能认定为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3.系争商标与外观设计相同或者近似关于系争商标与外观设计相同或者近似的判断,既能够就系争商标与外观设计的整体进行比对,也能够就系争商标的主体显著部分与外观设计的要部进行比对。有关系争商标与外观设计相同或者近似的认定,原则上适用商标相同、近似的审查标准。外观设计专利中的文字仅保护其特殊表现形式,含义并不在专利权保护范围内。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2002年7月22日关于取得外观设计专利的“蒙古醉”“蒙古小烧”是否违反《商标法》禁用条款问题的批复明确指出,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标明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为准,文字的字音、字义等内容不能作为要求保护的外观设计专利权的范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新乡市步云鞋垫有限责任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一案中也明确指出,尽管步云公司在争议注册商标前的1997年、1999年、2001年就获得外观设计专利权,但由于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范围是图片或照片中的外观设计,故在本案中受专利权保护的对象应为步云公司产品外包装袋的图案设计。争议商标中“彩步云”文字及云朵状的图形在外观上与步云公司获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图案或其中含有“步云”“鑫步云”字样的图案完全不同,争议商标没有构成对步云公司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损害。4.系争注册商标申请人没有取得外观设计专利权人的授权系争注册商标申请人应当就其主张的取得外观设计专利权人授权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三)在先姓名权未经许可,将别人的姓名申请申请注册商标,给别人姓名权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损害的,系争商标应当不予核准申请注册或者被宣告无效。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商标与别人姓名权相冲突:1.系争商标与别人姓名相同根据该条构成要件,系争商标必须与别人姓名相同才构成权利冲突,例如在“宗庆后案”中,安徽省某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宗庆后”商标,指定使用商品为第32类的“啤酒、矿泉水、饮料制剂”等。宗庆后是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因申请申请注册商标与别人姓名完全相同,因此商标局适用原《商标法》第31条(2013年《商标法第32条》)权利冲突的规定驳回申请。假如商标与别人姓名不完全相同但相似,该怎样处理?安徽省某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也申请了“何伯泉”商标,指定使用商品为第32类的“啤酒、无酒精饮料、矿泉水、汽水、果子粉、饮料制剂、茶饮料(水)、果汁、奶茶(非奶为主)、蔬菜汁(饮料)”。由于“何伯泉”与乐百氏(广东)食品饮料有限责任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何伯权的名字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不能适用原《商标法》第31条(2013年《商标法第32条》)的权利冲突规定驳回注册商标申请,商标局依据《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不良影响条款的规定驳回了商标注册申请。别人的姓名包含本名、笔名、艺名、别名等。《商标审理标准》规定,“别人”是指在世自然人。已故的自然人姓名是否能够未经授权就使用?我们认为,首先应该考虑商标使用的营利性特征;其次,应该考虑已故名人生活的时代。举例而言,假如有人把“杜甫”用做商标,没有人会将商品与杜甫建立什么联络;可是,假如有人以“毛泽东”或者“鲁迅”做商标,情形会大有不同。当然,即使是以“杜甫”为商标进行申请注册,也可能妨害公序良俗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要依据《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的规定进行审查。因此,我们认为,即使是已故名人的姓名也不能未经授权随便用做商标标识。2.系争商标的申请注册给别人姓名权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损害未经许可使用公众人物的姓名申请申请注册商标的,或者明知为别人的姓名,却基于损害别人利益的目的申请申请注册商标的,应当认定为对别人姓名权的侵害。这里假如使用的是公众人物的姓名,则不要求主观上有损害别人利益的目的,由于使用公众人物姓名本身主观上推定具有“搭便车”的故意,不当利用或可能损害公众人物的声誉。可是,假如是非公众人物,则强调其主观要件——以损害别人利益为目的。当然,现实生活中,别人以一名普通老百姓的姓名申请申请注册商标的情况很少,由于它对申请人而言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认定系争商标是否损害别人姓名权,应当考虑该姓名权人在社会公众当中的知晓程度。系争注册商标申请人应当就其主张的取得姓名权人许可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3.姓名是否具有其他含义假如姓名具有其他含义,而消费者是在其他含义下认识商标的,则不存在商标侵犯姓名权的问题。在“黎明”商标异议案中,香港著名影视歌星黎明对沈阳黎明发动机制造公司提出的“黎明”服务商标提出申请注册异议,认为该公司申请申请注册的商标侵犯自己的姓名权。可是,商标局认为,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黎明”指的是天快要亮或者刚亮的情况下,是现代汉语常用词,不属于独创性词汇。在中国有效申请注册的商标中,冠以“黎明”的商品在流通中,没有使消费者误认为与某人有关,从而驳回了黎明的异议申请,对“黎明”商标准予申请注册。(四)在先肖像权未经许可,将别人的肖像申请申请注册商标,给别人肖像权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损害的,系争商标应当不予核准申请注册或者被宣告无效。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商标与别人肖像权相冲突。1.系争商标与别人肖像相同或者近似别人的肖像包含肖像照片、肖像画等。“相同”是指系争商标与别人肖像完全相同。“近似”是指尽管系争商标与别人肖像在构图上有所不同,但反映了别人的主要形象特征,在社会公众的认知中指向该肖像权人。2.系争商标的申请注册给别人肖像权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损害未经许可使用公众人物的肖像申请申请注册商标的,或者明知为别人的肖像而申请申请注册商标的,应当认定为对别人肖像权的侵害。(五)在先企业名称权按照现行企业申请注册登记制度,企业名称中除了商号以外,还包含行政区划、行业特点和组织形式等要素。其中,商号才是企业真正的标记,其余3个因素则往往是在一定行政区划内与其他众多的企业所共同使用的东西,它们既不为其中任何1个企业所拥有,也不为这些相关的企业所共有。并且,这些东西既不具有私权的特征,也没有财产权的属性。主要是出于以往多年来行政区划或条块分割的便利,出于计划经济的必须,从计划管理的思维模式出发,人为区划市场的结果,因而实际上是政府主管部门强加在企业商号之上的附加标志。因此,企业名称中真正发挥区别功能的是商号,又称字号,是商事主体的文字表现形式,为该商事主体所专有,既是区别于其他企业的标记,又是企业的一项重要财产。因此,我们认为,应该统一使用“商号”的概念,而不是“企业名称”。在统一的商号概念下再区分已经登记的商号和没有登记的商号。假如商号与商标权发生冲突,是否所有的在先商号都优先于申请注册商标呢?河南省新乡市步云鞋垫有限责任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一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字号权”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当事人不能仅据此主张权利。步云公司将“步云”作为其享有的“字号权”,并据此主张在先权利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该案明确了字号非经登记为企业名称不受商标法规定的在先权利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申请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规定的商标权与其他权利冲突的权利类型中明确列举了“企业名称权”,该规定同样仅仅对登记后的企业名称在先于注册商标的情况提供优先保护。《商标审理标准》规定:将与别人在先登记、使用并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商号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文字申请申请注册为商标,容易导致中国相关公众混淆,致使在先商号权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对别人在先商号权的侵犯,系争商标应当不予核准申请注册或者予以撤销。其适用要件为:(1)商号的登记、使用日应当早于系争注册商标申请日;(2)该商号在中国相关公众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3)系争商标的申请注册与使用容易导致相关公众产生混淆,致使在先商号权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商标审理标准》明确要求商号必须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才能以在先性对抗注册商标。事实上,要求在先商号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混淆的内在要求,由于假如在先商号没有一定的知名度,相关公众也不会因申请申请注册商标的使用而可能产生商品来源混淆。因此,商标与在先企业名称冲突的适用要件其实主要是两个:第1个是时间要件,商号成立时间在先;第2个为后果要件,即商号与商标并存可能造成相关公众就商品来源产生混淆。时间的先后比较容易判断,但相关公众是否会发生混淆则必须综合考量客观情况得出结论。在上海避风塘美食有限责任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行政裁决审判监督案中,针对争议商标“竹家庄避风塘及图”商标是否侵害了上海避风塘公司的企业名称权,最高人民法院指出,“避风塘”一词不仅仅是上海避风塘公司的字号,还具有“躲避台风的港湾”和“一种风味料理或者菜肴烹饪方法”的含义,因此,只要不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上海避风塘公司就不能以其企业名称权禁止别人在“躲避台风的港湾”和“一种风味料理或者菜肴烹饪方法”的含义上正当使用“避风塘”一词。最高人民法院之因此作出如此判断,是由于综合考量了该案的具体情况。该案争议商标由竹子图案与“竹家庄避风塘”文字组成,其中竹子图案占据商标的大部分面积,且处于商标的显著位置。相对而言,“避风塘”在争议商标中并没有发挥识别作用。此外,对于餐饮行业相关公众而言,“避风塘”一词具有“一种风味料理或者菜肴烹饪方法”的含义,它本身起不到识别来源的作用。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争议商标的申请注册、使用不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也就没有侵害上海避风塘公司的企业名称权。
商标法中联想的可能的历史来源
从1964年开始设立工作小组起草欧共体商标法算起,欧共体《指令》的出台经历了20多年的历程。其间不乏多次修改建议稿。在最初的条文中,并没有“联想的可能”的表述。不过,最终在1988年成文之时,“联想的可能”却被载入《指令》文本。很大程度上,这被认为是比荷卢三国尤其是荷兰代表团在立法中的坚持以及比荷卢三国统一商标法以及判例影响所致。比荷卢三国的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几乎就是现代欧共体的缩微版和实验版。包含比荷卢统一商标法的制定以及统一的比荷卢法庭的建立都为欧共体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由于当时的比荷卢三国集中了包含飞利浦在内的上千知名品牌,其商标保护实践相对丰富,因而在当时的欧洲大陆,比荷卢三国的商标法(包含司法判例)被视为是最现代的。当时的比荷卢统一商标法对欧共体商标《指令》产生影响也不足为奇。不过,比荷卢三国统一商标法经历过多次修订,该法首次于1971年1月1日在三国正式生效,取代原来三国各自的商标法规。1983年11月10日统一商标法被修改,1987年1月1日生效;为了适应欧共体协调法令,比荷卢联盟于1992年再次修改了商标法并于1996年1月1日生效。从时间进程上看,1971年生效或者1983年出台的三国联盟商标法及相关司法判例对欧共体《指令》产生的影响最大。而后,欧共体《指令》反过来又推动了1992年出台、1996年生效的现行三国联盟商标法。在1971年的三国统一商标法里,并没有“联想的可能”的踪迹。1971年的比荷卢联盟商标法里与侵权判定最相关的第13条的规定,尤其是第13条(A)(1)法条的措词,和中国现行商标法第52条第一项几乎没有差别。其间没有“联想的可能”,也没有“混淆的可能”的表述,是其独特之处。相关的文献表明,1983年出台的三国统一商标法也没有“联想的可能”的规定。“联想的可能”的最初来源,多被认为是比荷卢法庭判例法,即1983年的Union/UnionSoleure案。其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比荷卢三国商标法的框架下,在没有“混淆的可能”这一概念的情况时,法庭怎样判断商标近似?这恰好也是商标淡化判定中同样必须面临的问题。“当考虑到个案的诸如商标的显著性的特殊情形,在整体观察与对比观察之下,假如标志与商标听起来或者看起来或者观念上达到这样一种相似性,以至于标志与商标间的‘联想’被激发,则标志与商标就是近似的。”而到了1992年修订,1996年出台的比荷卢商标法第13条(A)(1)(b)里,则明白无误地将“在商贸活动中将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使用在与申请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上,使公众在使用标志与申请注册商标之间存在着‘联想的可能’的行为定性为侵权”。尽管1996年版的比荷卢商标法是为适应《指令》而修订,可是第13条(A)(1)(b)的规定不能当然地理解为体现了《指令》的精神,其表明的仅仅是比荷卢三国对于《指令》的理解。比荷卢三国对于《指令》的这种理解能够一直追溯到《指令》的立法进程。事实上,在指令出台的整个过程中,就侵权判定采用“混淆的可能”还是“联想的可能”的问题,比荷卢三国的立场与欧共体其他国家的立场分歧严重,比荷卢三国偏向于“联想的可能”,即当相同或者类似的商标使用在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上时,并不必须在相关公众中产生混淆,而只要产生了联想,商标权人就有权禁止。这显然比“混淆的可能”的判断标准要宽泛。在欧共体其他国家看来,这种过度的保护显然与自由贸易的目标背离,因此极力反对。最终形成的《指令》第4条、第5条代表了这两种观点的折中,但其措词令人困惑。由于一般而言,仅有大的概念包含小的概念。假如认为“联想的可能”比“混淆的可能”更为宽广,那么怎样理解“混淆的可能”能够包含“联想的可能”?比荷卢三国认为,这一表述宣布了“联想的可能”的判断标准的胜利。或许是由于这一原因,1996年的比荷卢三国商标法里的措辞直接使用了“联想的可能”的表述,而没有提及“混淆的可能”。然而,这种胜利宣言为时过早,立法上措词的妥协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由于《指令》的条文解释最终取决于欧共体法庭(ECJ)。不幸的是,直到比荷卢三国商标法生效之后的1997年,ECJ才有机会在Pumav.Sabel(C‐251/95)案中对于“联想的可能”的理解做出正面回应。使比荷卢三国沮丧的是,AGJacobs在其意见书中断然否认《指令》立法进程中的谈判备忘录能够作为解释《指令》的依据。随后一系列的欧共体法庭案例表明,比荷卢三国认为在《指令》中“联想的可能”取代“混淆的可能”的理解遭到完全的否决。在此之后,比荷卢三国商标法中“联想的可能”的条款13(A)(1)(b),在2004年的比荷卢三国知识产权法(商标与外观设计)修订的过程中,也被完全取缔。其修正后的相关条款的表述,与欧共体《指令》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