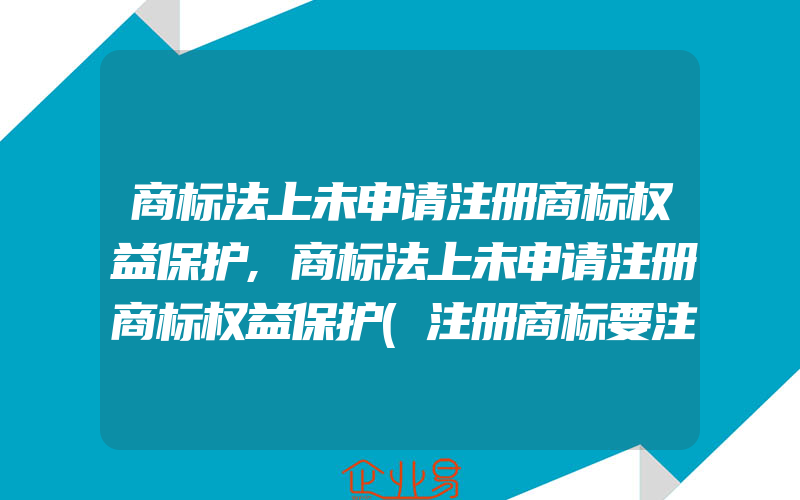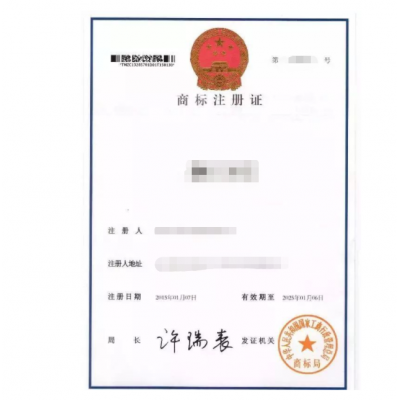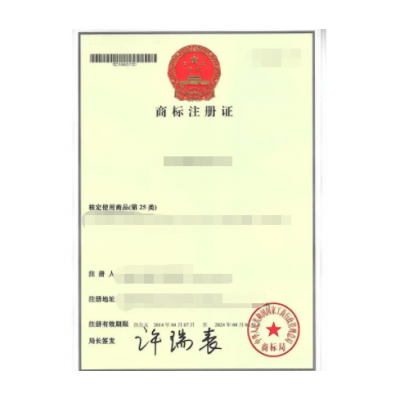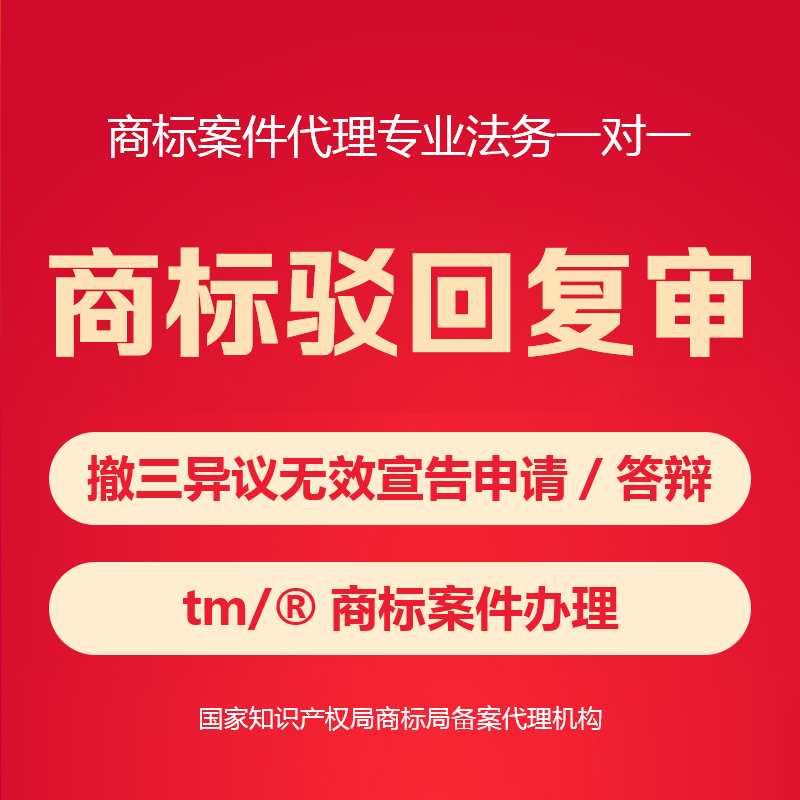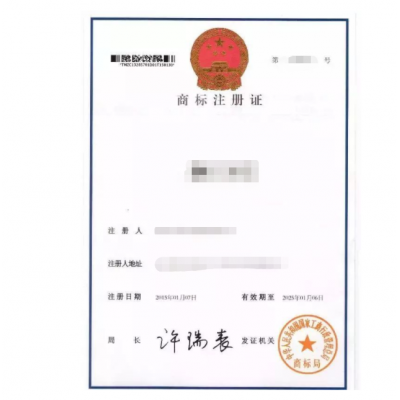商标法上未申请注册商标权益保护
恶意抢注治理规则的核心是将“恶意”作为抢注行为违法性的判准并导向不利法律后果。尽管表面上“不予申请注册并禁止使用”更有利于保护未申请注册商标权益,但法律后果应当统为“不予申请注册”。下文将从两个方面论证该观点:商标法理论怎样调和未申请注册商标权益与申请注册取得模式;制定法上怎样处理当前采取“不予申请注册并禁止使用”法律后果的《商标法》第13条第2款、第3款与第15条第1款。商标法上未申请注册商标权益保护的应有姿态商标法在处理申请注册商标权与未申请注册商标权益时应当具备不同姿态。前文已述及区分商标抢注与恶意抢注的制度意义,换言之与申请注册取得模式伴生的先申请原则本身是鼓励抢注的,(参见钟鸣、陈锦川:《制止恶意抢注的商标法规范体系以及适用》,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10期,第8页。)这与申请注册制的功能有关。前现代与现代知识产权法的1个显著区别在于其基本理念从“创造”到“对象”的系统转向。这种转向的特征在于,法律不再建立在对创造性劳动过程的田园牧歌式的描摹之上,而是集中在“作为1个闭合和可靠实体”的保护对象的经济价值和社会贡献之上,因而能够从1个更加广阔的视角看待知识产品的合理分配。(参见[澳]布拉德谢尔曼、[英]莱昂内尔本特利著:《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演进:英国的历程(1760-1911)》,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6-210页。)知识产品也不再仅仅是一种难以厘清排他边界和明确支配的自然事实,而是可被纳入现代权利框架的制度性事实。为了构建这种条理清晰、范围明确的权利框架,申请注册、登记等具有潜在自组织性的制度工具应运而生。通过申请注册程序,法律得以尽量清晰地划定权利的边界。通过鼓励“抢先提出申请注册”,商标法实际上意欲将未申请注册商标“驱赶”向能够确保权利安定性和交易安全的申请注册状态。(参见余俊著:《商标法律进化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137页)因此,尽管脱胎于反假冒制度的商标保护贯穿未申请注册商标和申请注册商标,并且以商誉作为协调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抓手,(one,RobertG,HuntingGoodwill:AHistoryoftheConCEptofGoodwillinTrademarkLaw,BostonUniversityLawReviewvol.86,no.3(June2006pp.572-575)可是,优先保护申请注册商标是商标法的应有姿态。这种姿态的实现必须如下保障。首先,在商标法的场域内,以“申请注册与否”来区别权利义务的安排模式,除非符合严苛的例外条件,仅有申请注册商标权利人享有禁止使用请求权。商标法通过申请注册行为构建了封闭的有名权利,并预先规定了该权利的取得条件和保护范围,从而显著降低了界权成本。质言之,申请注册取得制是将个人“占有”商标并获取排他权利的意志,以成本较低的方式与别人意志相协调的结果。由于本质上相互平等的个人意志与这种意志的彼此协调共同构成了权利取得的整体条件,从而导致找寻外在事物对别人的重要性皆为一律的统一评价(参见朱庆育:《权利的非伦理性化:客观权利理论以及在中国的命运》,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第18页。)—亦即就自己获得排他性权利之事实取得别人“同意”这取得权利的过程无法单纯依据个人的主张来完成。在商标法的情境下,这种整体条件的理想状态就表现为商标权取得的递进式条件:(1)个人通过中立性劳动(使用商标)创造商标符号并主张权利;(2)对中立性劳动进行理性批判以明确权利。很明显,从规范角度看满足该条件的关键在于第2步。因此,能够得出两个推论:其一,申请注册制将部分证明成本转嫁给申请注册机关,(包含商标符号本身的合法性—体现为绝对禁止申请注册事由,以及商标权利的合规范性—体现为相对禁止申请注册事由。)并利用公示制度构建商标权利信息平台,令个人更容易地完成获权意思表达的宏观建构,以协调别人的平等意志。因此,一旦申请注册商标与未申请注册商标获得同等保护,即无法实现《商标法》的立法目的。其二,上述成本转移方式以劳动与劳动之理性批判的相对分离作为前提。(申请注册机关事实上假定利害关系人(在先使用者)最关注商标权利合规范性之检验,于是进1步将提出反对意见的成本转移给不同意申请注册者获权主张的人,通过程序分流(受理根据相对禁止申请注册事由提起的异议、撤销和无效宣告请求,而不是一概主动审查)降低申请注册机关的审查成本)
商标法上未申请注册商标权益保护
申请注册制度只是一种框架假定:商标注册申请人最终会通过使用行为创造商标符号意义,并实现商标功能。继而对劳动之理性的审査就成为预先推定,而非对既存中立性劳动的事后检验。因此,申请注册制度必须促使“理性”与“劳动”重新吻合在一起。措施之即反对恶意抢注(另一重大措施即为申请注册取得模式必须伴随的“使用强制”要求。从弥合申请注册与使用要求的总体视角看,授权确权阶段对恶意抢注的排除可谓“前封”,使用强制要求可谓“后攻”。):假如商标权人的初始目的就是利用这种理性与劳动相对分离的状态知晓别人未申请注册商标存在,仍然抢先要求明确权利,则必须赋予其不利法律后果。将该措施的直接目的坐落在对抢注行为违法性的消极评价或是积极保护未申请注册商标杈益,即为上述商标法的姿态问题。显然,商标法求取权利的安定性,依靠的是前者而非后者采取这一姿态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未申请注册商标没有经过获权意义上对商标使用行为的理性批判。因此,商标法受该直接目的所指引,只能通过提供“不予申请注册”请求权的方式间接、有限地保护未申请注册商标。其次,应当认真对待申请注册商标权,留下一部“干净”的《商标法》。质言之,商标法在设定权利义务时必须“厌恶”未申请注册商标。部分未申请注册商标因凝结商誉而具备财产价值但商标法不应将其视同申请注册商标。第一,整部《商标法》应当围绕商标财产权利的取得、维持、行使和消灭展开,打开该场域的钥匙即为注册商标。因此,作为财产法的商标法一般只能以拒绝别人恶意抢注的方式间接保护未申请注册商标权益。这么做的原因在于未申请注册商标权益本质上不是财产权。从财产权的理论构架上看,学者将对象与权利的关系化约为“财产体”与“财产权”,通过这种区分,财产权制度具备特殊的形式价值。然而,二者相对分离必须满足两个前提:作为处分对象的财产体的内容和范围是明确的,以及存在占有之外财产权变动的表征方式。(参见冉吴:《制定法对财产权的影响》,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5期,第11-12页。)因此,申请注册而非使用协助完成了商标符号的从共有到私有,这与前文所述“劳动的理性批判”同义。而未申请注册商标未能完成这一特定化和公示过程。继而,从法律关系的形式上看,商标法原则上只能为申请注册商标设定禁止使用请求权。反过米说,在该法的视野中,未申请注册商标仍然处于共有状态,亦即向所有人敞开胸怀,任何人都有权使用”。(Seneca,Octavia.u.402f,inSeneca'sTragedies.Tans.F.J.Miller(London,Heinemann.1917,i439转引自[澳]斯蒂芬巴克著:《自然法与财产权理论:从格劳秀斯到休谟》,周清林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当然这并不妨碍其他法律提供禁止权。第二,更新认识商誉要素在商标法中的地位。一方面,商标法只能通过商标权间接保护商誉,而非越过该权利明确过程直接进行保护:另一方面,商标法应当通过“使用强制”确保商标权利框架被商誉所填充,防止出现“僵尸权利”或“标识财产权”。因此对商标法而言形成商誉是法定义务,而不是请求权基础。(对于驰名商标特殊保护,商誉是请求权基础,这是由于商誉积累使得商标功能发生质变。)总而言之,商标法的具体条款假如不加区分地平等保护未申请注册与申请注册商标,是对该法基本价值取向的盲目和恣意,严重背离了预先划定商标权利边界的制度设计。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