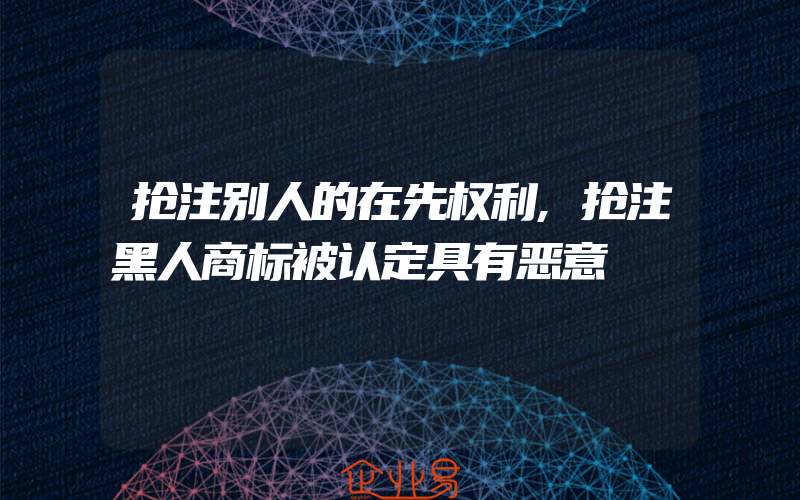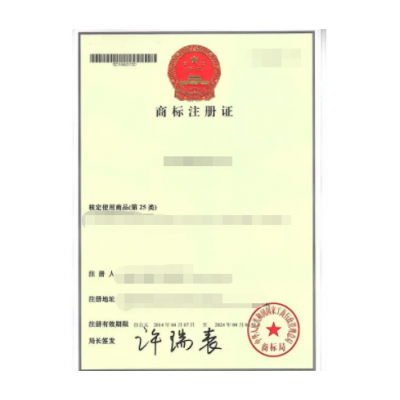抢注别人的在先权利
在先权利在商标确权行政程序中的地位问题,是中国商标法上的独特问题。⑥在“功夫熊猫”案⑦中将“商品化权”这一概念明确列为第32条前段的“在先权利”,进1步引起了实务界与学界的广泛探讨。⑧我国商标法中的“在先权利”概念滥觞于《巴黎公约》第6条之五B小节中列举的三项拒绝(无效)理由。其中的侵犯第三人的既得权利,能够是在有关国家已经受到保护的商标权,或者其他权利,例如对厂商名称的权利或著作权。假如一项商标侵犯了人身权,则本项规则也能够适用。⑨在《授权确权规定》第18条中将“在先权利”定义为:包含当事人在诉争商标注册申请日以前享有的民事权利或者其他应予保护的合法权益。将其进行了扩大解释则不仅仅限于所谓的绝对权,而将合法权益也纳入了其中。在实践中,对于《商标法》第32条前段中的“在先权利”争议较大的问题集中两方面:其一是与自然人姓名、肖像以及法人名称等的关系;其二是与电视节目名称、角色名称和形象等的关系。以下将分别予以论述。1.与自然人姓名以及法人名称等的关系作为“在先权利”之一的自然人姓名权益,在中国商标法上体现出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其阻却别人申请注册的权源并不是来自于人格权理论,而是来自于商业标识法的理论。对此,在“乔丹”案⑩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适用《商标法》第32条保护别人在先姓名权时,相关公众是否容易误认为标记有争议商标的商品与该自然人存在代言、许可等特定关系,是认定争议商标的申请注册是否损害该自然人姓名权的重要因素。该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乔丹”在中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我国相关公众通常以“乔丹”指代再审申请人(即美国篮球明星MichaelJeffreyJordan),并且“乔丹”已经与再审申请人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对应关系。以此案为依据,《授权确权规定》第20条规定,当事人主张诉争商标损害其姓名权,假如相关公众认为该商标标识指代了该自然人,容易认为标记有该商标的商品系经过该自然人许可或者与该自然人存在特定联络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商标损害了该自然人的姓名权;而对于当事人以其笔名、艺名和译名等特定名称主张姓名权的,“该特定名称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与该自然人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相关公众以其指代该自然人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人格权理论与商业标识法理论较为显著的区别就在于,怎样处理同名同姓的人在商业活动中使用姓名的问题。从姓名权的角度则不能解决假冒者将自己的姓名改成与知名作家相同的姓名,其次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上署上该姓名,从而引起混淆的问题。在“王跃文诉叶国军、王跃文等”案①中,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可是并不构成“假冒别人署名的作品”。由于在作品上署的是作者的“合法姓名”,而没有冒用别人的姓名。可是从反不正当竞争的角度看,法院指出,作为文化市场的经营者,作者往往通过在作品上署名,来传扬自己和自己的写作方式。消费者选购图书时,作品题材和作者是其考虑的主要因素。知名作家在作品上的署名,已经成为图书的一种商品标识,发挥着指引消费者作出消费决定的重要作用。知名作家的署名一旦被借鉴、仿冒、攀附或淡化,就可能引导消费者作出错误的消费决定,从而影响到署名人的正当权益,因此,这些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2.与电视节目名称、虚拟角色名称、形象等的关系对于电视节目名称、虚拟角色名称、形象等在申请注册环节的相关问题,在中国商标法下是以“商品化权”予以解决的。早期我国下级法院曾较为普遍地依据人格权理论,将自然人姓名权或肖像权的商业化利用活动纳入人格权保护范围,而对于非自然人客体的商品化问题,在“功夫熊猫”案②中首次在判决中将“商品化权”这一概念明确列入第32条前段的“在先权利”范围,进而构成驳回申请注册的异议事由。我国司法实践中所使用“商品化权”概念不同于美国学说上普遍承认的“形象公开权”概念,也不出自德国一般人格权之实践,是1个具有独创性质的概念体系。特别是在《授权确权规定》第22条第2款中,将司法实践中的判例法理上升为司法解释,即对于著作权保护期限内的作品,假如作品名称、作品中的角色名称等具有较高知名度,将其作为商标使用在相关商品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其经过权利人的许可或者与权利人存在特定联络,当事人以此主张构成在先权益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当然,在这一司法解释中,为了防止商品化权的扩大化适用,在商业标识法目的的基础上在要件上作出了限制,例如要求“对于著作权保护期限内的作品”。而对于“著作权保护期限以外的作品”,除非依据“其他不良影响”条款以将公有领域的符号资源申请申请注册为由予以驳回外,并不能依据商品化权予以处理。从上述论述能够看出,我国司法实践的进路,是注意到了在先权利中可能包含的三种客体(包含自然人的商品化权问题、物之影像和名称的商品化权问题以及虚拟角色等的商品化)间所具有的共性,特别是所面对的利益关系的一致性,因此试图建立统一化理解。在分割化理解下,提供的可供选择的三种理论备选中,由于人格权理论天然地排除了自然人以外的客体,作为商品化权保护客体的可能性,因此,仅有顾客吸引力学说与商业标识法体系能够提供可能的统一化选项。从现实的利益关系看,不管是自然人的商品化权还是物或者虚拟角色等的商品化权,都是通过对于顾客吸引力的保护,防止别人擅自搭便车行为的发生而设置的排他权。这一过程并不是通过立法而实现的,而是通过司法实践创设的。可是,顾客吸引力学说下的统一化尝试最大的质疑就是有违“物权/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对于别人的智力成果或商业信用的搭便车行为,原则上是并不予禁止的,人类社会也正是由于这种搭便车行为才逐渐走向了文明与进步。可是原则上的自由,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设置禁止别人搭便车的例外,例如,为了确保创作活动的激励,使得文化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这些更为宏观的功利目的不会受到阻碍,因此,当设置著作权和专利权的保护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大于容许这些法定的垄断权带来的弊端时,才会容许上述排他权的设置。在设置程序上应该通过民主程序,特别是立法予以明确,以使得被限制搭便车自由的第三人能够提前预期其行为,在立法尚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司法应该保持相当的谦抑,这也是所谓知识产权法定主义的初衷。就顾客吸引力学说下,对于商品化权的设权过程来看,对于大部分虚拟角色的形象等可能能够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而对于虚拟人物的名称也能够在推向市场伊始,就进行所欲商品化的商品类别的商标注册申请,将其转化为既有的为立法所确认的法定权利。在商品化权益主体没有申请注册商标,或其客体无法寻求既有权利保护时,企图通过顾客吸引力这一学说创立一种排他权的做法都有损于法的安定性与可预见性。而中国司法实践的做法,则是转向了商业标识法的统一化理解。即不管是对于虚拟角色等的商品化权,还是对于名人的姓名或肖像的商品化权,假如别人擅自将其用于商品化产品的开发与销售或作为宣传广告的手段代言其他产品,那么对于上述主体以许可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将受到侵害,因此,商品化权客体下的利益纠纷状况应该是相似的。而对应这种相似利益状况的调整模式从商业标识法中的商业标识的功能角度出发,不管是从来源识别功能、品质保证功能,抑或是宣传广告功能出发,对统一理解大有裨益。③对于商业标识法体系下的商品化权统一化尝试,其最大目的就是进1步推进顾客吸引力学说,使得既有的商业标识法保护体系能够得以适用,因此摆脱知识产权法定主义的桎梏。但对其最大的质疑就是,从现实上看,许多商品化活动中的实践很难套入商业标识性使用等具体要件。到底何种情况下对虚拟角色名称等的商品化使用活动,构成商业标识法意义上的混淆行为,可能有待于商标法在申请注册环节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侵权环节予以具体化。
抢注黑人商标被认定具有恶意
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案情简介】“DARLIE黑人”品牌,由好来化工(中山)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好来公司)创立,品牌发展至今,已在口腔护理用品业具有一定的知名度。“黑人”中文商标、“DARLIE”英文商标和图形商标的商标权人为好来公司,图形的著作权人为好维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好维公司)。“黑人”系列商标无效宣告案件中,原告杜某某于2002年分别在蚊香、诱杀昆虫电力装置、纸巾等商品类别上申请了多件商标。除此之外,杜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广州市黑人日用品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广州黑人公司)还在电加热装置等商品上申请申请注册商标,商标标志即为上述黑人图形商标中的人物形象。好来公司及好维公司就杜某某申请的上述商标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下称原商标评审委员会)提起无效宣告申请,原商标评审委员会支持了好来公司及好维公司的申请,裁定上述诉争商标无效。杜某某及广州黑人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该系列案件的一审判决。【法律分析】该案主要争议焦点涉及到我国商标法中“其他不正当手段”的认定。我国商标法关于其他不正当手段并未做明确的规定,商标法实施条例也未做进1步的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就进行了相应的细化,“其他不正当手段”能够包含如下情况:扰乱注册商标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今年4月24日发布的《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对什么叫“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申请注册”进行了规定,主要包含以下情形:1.诉争商标注册申请人申请申请注册了多件商标,并且其申请的商标与其他主体的知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2.诉争商标注册申请人申请申请注册多件商标,并且其申请的商标与其他主体的名称、有一定影响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等商业标识相同或者近似;3.诉争商标注册申请人有兜售商标的情形;4.诉争商标注册申请人高价转让商标没有成功,之后便向在先商标使用人提起侵权诉讼。上述审理指南对“不正当手段取得申请注册”的情形做出了更具实践意义的规定。具体到此案,杜某某以及公司申请注册的商标共计66件,且仅在2002年4月11日当天就申请申请注册了37件。杜某某以及公司申请注册的商标涉及行业类别跨度大,其中53件商标与别人享有在先权利构成相同或类似,部分在先商标曾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例如,在多个商品类别上申请申请注册了“黑人”、“DARLIE”商标,还申请申请注册了“多芬”“珍妮诗”“亮莊”“CleanClear可伶可俐”“拉芳”“采乐”“SKⅡ”等商标,例如“珍妮诗”牌餐巾纸、“亮莊”牌纸尿裤“CleanClear可伶可俐”牌杀虫剂“SKⅡ”牌杀虫剂等。杜某某以及公司申请的前述系列商标与别人的知名商标构成相同或者近似,其申请注册行为具有明显的复制、抄袭别人高知名度商标的故意,扰乱了正常的注册商标管理秩序,有损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因此,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定杜某某及广州黑人公司申请注册诉争商标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以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注册的情形。判断诉争商标是否属于以“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注册的情形,并非仅考虑某一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情况,而应着眼于诉争商标注册申请人的一系列相关行为,正是由于申请人的恶意申请注册行为,扰乱了正常的注册商标管理秩序,损害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因此对其不正当申请注册的商标予以无效宣告。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