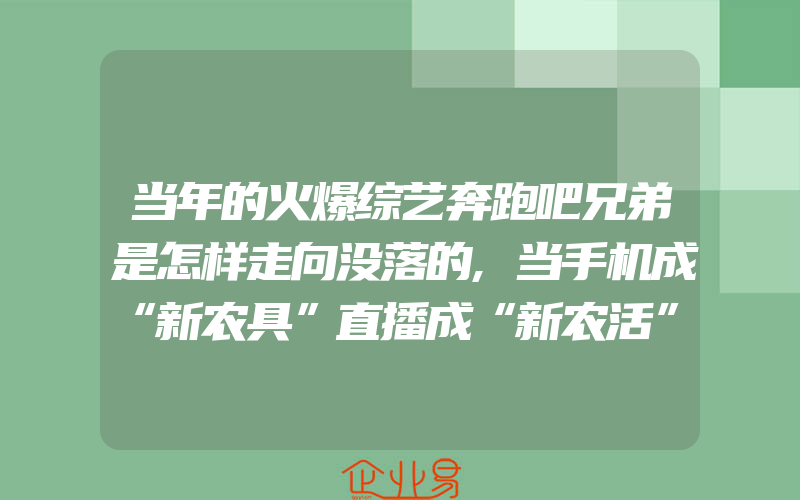当年的火爆综艺奔跑吧兄弟是怎样走向没落的
《奔跑吧兄弟》是一档热门综艺节目,曾经一度风靡全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节目的收视率逐渐下滑,终陷入了没落。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奔跑吧兄弟》的没落呢?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1. 讲究卡司不讲究内容
《奔跑吧兄弟》一开始的成功,离不开里面的一众卡司,比如邓超、郑恺、陈赫等明星的加盟,让这个节目成为全民热议话题。随着节目的不断推陈出新,卡司的阵容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可是,新的卡司人员往往难以与旧的卡司匹配,而且节目的主要内容也没有进行创新和更新,导致观众的疲劳感逐渐增加,失去了继续观看的动力。
2. 缺少剧情与情感因素
《奔跑吧兄弟》一开始便以“兄弟情”为核心,在卡司之间的默契与配合形成了非常强的感情元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观众发现节目长期依靠游戏为主,缺乏情感元素的加入,这导致节目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失去了观众的认同感和共鸣感。
3. 贴近生活的游戏内容逐渐丧失
节目一开始以户外生存游戏为主,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了人们的生活,让观众有参与感。随着游戏形式的更新换代,以及部分游戏与生活的脱离,观众的兴趣逐渐下降。而且,部分游戏内容过于奇葩离谱,让观众的观感产生疲惫感,加上与兄弟间情感的深入发掘,导致了观众对于节目的逐渐疏远。
4. 疲于奔跑,难于撑得下去
《奔跑吧兄弟》曾经以疯狂的奔跑和兄弟的默契冲刺取得了巨大的收视率。但是,这也慢慢变成了一种艺人的制作生命消耗方式,表演者不仅要承受体力上的压力,还需要承受暴露的压力,这样的方式真实地消耗着每一位艺人所剩余的能量,也让他们不能承受太多这样的任务。
总而言之,《奔跑吧兄弟》的没落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卡司到内容、从游戏到情感,这篇我们着重分析了其中的几个因素。尽管他们在短期内能够吸引大量粉丝和观众的注意,但长期来看,节目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新的亮点和永续性的吸引力,就很难从太阳到寒冬,维持起一份很好的受众关系。
当手机成“新农具”直播成“新农活”
近日,某知名教育培训品牌农产品直播带货的视频冲上网络热搜,在热烈的点赞声中,也有网友质疑直播间里“一根玉米卖6元钱”太贵,带货农产品的价格普遍偏高。
随着数字经济兴起,直播带货不再是明星的“专属领域”。在我国广袤的农村,一些农民抓住机遇,把手机当成“新农具”,把直播当成“新农活”,以田间地头为布景,以绿色生态为卖点,推销售卖农产品。在农产品直播带货过程中,普通农民的收益究竟如何?如何让农民在直播链条上获得更多的实惠?
山东寿光的新型职业农民张先生家里有近5亩地,主要种植西红柿、黄瓜等瓜果蔬菜。他勤于钻研农业技术,也曾通过直播平台销售自家种的瓜果蔬菜。去年,他种的一款口感较好的西红柿,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的最高价格是传统渠道售价的三四倍。
张先生说:“我在当地卖,就是四五块钱一斤,通过直播宣传,然后加一些内容进去,(最高)就卖到了二十四块钱一斤。这个不是我去做的,我邀请了几个电商过来,他们在我这进行直播,他们就翻好几番。”
起初,张先生也曾在直播平台上卖农产品,甚至在电商平台上开了店做直播。后来他转变了思路,将农产品交给专业的直播团队销售。和电商直播平台合作,并没有谈具体的销售分成,而是简单地批发给电商团队,由其作为代理商网上直播带货。
“同样是我的产品,我种出来的果实,我应该是最知道的,我就把这个产品概念跟主播说了,主播就把概念分享给他的粉丝,实际上就是他在中间做了转播(转卖),他把价格提到了3~4倍,他就有销量。”张先生说。
找代理商做直播带货的模式也没能长久。张先生说,真正在直播平台上销售农产品的,大多数是脱离农业种植的新生代。一边在网上做直播销售,一边又在田间地头耕种的农民,占比数量较少。
此外,在张先生看来,部分农产品在电商平台的销售价格翻倍,虽然利润可观,但分成给普通农民的利润并不高,“他有包装、有运输,连包装带物流人家都包了,但是我知道他的利润肯定要高很多。总的来说,他卖24,我一斤才挣两块,他最少一斤挣十五元。平台经营者首先考虑的是利润点,不会考虑到底是助农、帮农。”
多位农民告诉记者,农民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农产品,看着热闹,但实际惠农效果有限。首先对普通农民来说,电商直播的技能门槛较高;其次,在电商平台开店也有一定的成本。销售流量也并非普通农民简单在平台上开店就能轻易获得。
刘丰春从事农村电商培训多年,培训对象主要是农民。他告诉记者,在电商直播链条上,农民获得的利润比较微薄,“他们挣的钱很微薄,不多的。直播链条非常长,有些可能需要冷链,需要物流,需要有人卖货,需要包装。农民可能就是种植,把农产品种出来了,但是后面的环节,可能他也都没办法参与。”
刘丰春以种植红薯举例,如果农民在传统渠道销售,大多1斤只卖八毛钱到一块钱,而拿到直播平台上销售,1斤的零售价可以3~4元。这其中,快递、包装、仓储物流到广告销售等环节的成本较高。
刘丰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红薯(成本)一块,快递基本上得一块,店铺的运营成本,打广告又在一块,还有纸箱的费用。红薯其实是最简单的初级农产品的,也不怕坏,直接包装。如果是桃子或者樱桃,它的成本会更高了,里面得有防冻的冰袋。如果说在直播上可能成本会更高,(其中有)直播人员的分成,我估计一斤合下来都得两块。其实红薯本身的成本是低的,整个运营过程占了大量的成本。”
刘丰春认为,在直播产业链条中,只有解决了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等问题,农民才能在直播带货的产业链分成中拥有更多话语权和议价筹码。除非直播的农民自己是网红,但网红农民显然无法“批量化生产”。
刘丰春说:“规模化和规范化都跟不上,农民就没有很好的议价权。现有的这种结构情况下,如果说老百姓这边种了10亩,那边种了10亩,然后下面人把它收过来,快递成本还是没有办法降低,运营成本可能也没有办法降低。”
农学专业本硕毕业的代明亮自主创业做了一家公司,专注订单农业的探索与实践。作为一名业内人士,据他的观察,虽然电商平台迅速发展,很多地方的农产品也想借助电商渠道增加销量,赢得更多收益,但农民获得的收益有限。
代明亮说:“广泛的农民,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还没有通过直播电商来获得比较明显的平均收益。农民的价值收入,在离开土地把农产品交给第一手收购商的时候,他的利润就终止了,跟他就没有关系了。”
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这需要专业的力量和团队来组织。代明亮告诉记者,他看好“订单农业”,这种模式可真正实现产销环节无缝对接,既让农民获得更大收益,也让消费者获得实惠,“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把农民的利益和直播方的销量相对更加直接、更加密切联系,他的利益收入才能够给到这边。‘订单农业’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三农问题”专家徐祥临认为,让农民增产又增收,在电商直播平台上获得更大收益,应把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融为一体的“三位一体综合合作”体系建立起来,也就是把农民按地域、成体系地充分组织起来,成立服务功能齐全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社。
徐祥临说:“它能够解决农民生产技术上的难题,购买销售的难题,金融保险的难题,能够让农民分享全产业链的增值收益。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它就会解决过剩问题,它能够解决农产品的质量问题,能够满足市场规模化、生产标准化的要求。”
去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央农办等四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到2023年6月底,打造若干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三位一体”试点单位。试点工作为期两年,现已正式开始。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